离开堕落的边缘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太幼稚了,或者太天真了,总是在错过中发现自己错过了,总是在憧憬中做着未必应该做的事,总是在一个晴朗的天空默默地忧伤。有时觉得一个人生活会很好的,就像那飘落在人行道两旁的树叶,没有束缚,没有被迫,在一个可以独处的地方遥望着没有边际的天空,想着自己被风托在空气中的感觉,慢慢地享受那属于它属于心的空间。
但是,当我一个人走了一天后,才发现一个人过两个人曾经过的生活,一个人走两个人曾经走过的路,一个人坐在本属于两个人的位子是如此的让我不堪一击。或许当初不应该这样大度,把自己的生命分给另外一个人,让自己陷入那为自己而设的围城,愈陷愈深,有点窒息。
静静的穿过草地,在一个有阳光的日子里我去寻找那遗失的角落,感受着阳光依然明媚,小草依然柔弱。真的应该一点点舍弃,不应该记起那清脆的小草被折腰的声音,像留下的脚步,我没有想过让它为自己记录曾经有过的岁月,也没有想过让它成为生命中一个可以让自己伤心和无助的起点。
回头再看那地下,没有留下,我告诉自己。也许只有这样我才能让自己平静下来,才能够怀着曾经虔诚的心期待着属于自己的,而不是未必属于我的。离开草地,我努力使自己忘记我永远都不要想起的岁月,过去了终究是过去了,如果还刻意去寻求,只会让自己沉沦于回忆中,心甘情愿的接受折磨。这样的一天,我一个人把曾经不属于一个人的路走过,让记忆中残留的碎片“灰飞烟灭”,没有重新组合的将来。我苛责自己,是否应该原谅自己?
抬头,几天来阴沉的天空被这温馨的日光驱散,一股气息直往鼻孔里钻。就像五月的槐花,淡淡的,清清的,一屡香气。
后来与朋友聊天中听朋友说一句话,心若在一起,空间就不是距离,我想了很多,晚上我披着衣服靠在阳台上,看着远处若隐若现地霓虹灯,我问自己,什么叫距离,为什么存在距离?既然心在一起,又何必谈到距离?爱过,恨过,爱恨之间,时间在一步一步隔膜我们,时间在一步一步淡化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却在我没有预料中来到。打破了距离,视线一点点开始模糊,两颗心在逼近,可怜的是,距离却在把那无形的网络罩在柔软的身躯。我想这应该是一种考验吧,心真在一起,就不怕有距离,就不会躲在一个凌空的角落,躲避那本不应该躲避的事实。
偶尔也会想起那很久以前的日子,想起一个人孤独寂寞地骑着单车穿过那单薄的青春岁月。可能真的没有可以让人忘记的东西,想忘记,就不要想起,想起,就不会忘记。而自己被回忆拉回的时候,眼神忧郁的在告诉世界,或者真的有过。“死党”杨峥曾经和我一起探讨那本不应该探讨的理论,那时候他刚和他那个分了又和、和了又分、分了再和的女朋友分手,人有点不可理喻,有点不可思议。我当时是笑谈人生,静静的享受这没有分手的日子。我们又融合在一起,为了彻底返回那个灿烂的岁月,我劝他:“在这个世界上,当你发现别无选择的时候,你必须试着去接受一种事实。”他含情默默的看我一会儿,“鲁迅爷爷说的对,‘世上大多半男人本来应该做圣贤的,结果全被女人给毁掉了。’”我*!老师让他背这段课文的时候他死活背不下来,现在一字不差!
人应该学会疗伤,当你从那围墙上摔下来的时候,难免伤痕累累,这时候最大的帮助就是自己疗伤,逃离了围城,远离了堕落的边缘,又是一个自己,又是那个活在灿烂和明媚里的生命!
流浪书生(未必)
2005年01月02日于旷野斋
离开堕落的边缘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太幼稚了,或者太天真了,总是在错过中发现自己错过了,总是在憧憬中做着未必应该做的事,总是在一个晴朗的天空默默地忧伤。有时觉得一个人生活会很好的,就像那飘落在人行道两旁的树叶,没有束缚,没有被迫,在一个可以独处的地方遥望着没有边际的天空,想着自己被风托在空气中的感觉,慢慢地享受那属于它属于心的空间。
但是,当我一个人走了一天后,才发现一个人过两个人曾经过的生活,一个人走两个人曾经走过的路,一个人坐在本属于两个人的位子是如此的让我不堪一击。或许当初不应该这样大度,把自己的生命分给另外一个人,让自己陷入那为自己而设的围城,愈陷愈深,有点窒息。
静静的穿过草地,在一个有阳光的日子里我去寻找那遗失的角落,感受着阳光依然明媚,小草依然柔弱。真的应该一点点舍弃,不应该记起那清脆的小草被折腰的声音,像留下的脚步,我没有想过让它为自己记录曾经有过的岁月,也没有想过让它成为生命中一个可以让自己伤心和无助的起点。
回头再看那地下,没有留下,我告诉自己。也许只有这样我才能让自己平静下来,才能够怀着曾经虔诚的心期待着属于自己的,而不是未必属于我的。离开草地,我努力使自己忘记我永远都不要想起的岁月,过去了终究是过去了,如果还刻意去寻求,只会让自己沉沦于回忆中,心甘情愿的接受折磨。这样的一天,我一个人把曾经不属于一个人的路走过,让记忆中残留的碎片“灰飞烟灭”,没有重新组合的将来。我苛责自己,是否应该原谅自己?
抬头,几天来阴沉的天空被这温馨的日光驱散,一股气息直往鼻孔里钻。就像五月的槐花,淡淡的,清清的,一屡香气。
后来与朋友聊天中听朋友说一句话,心若在一起,空间就不是距离,我想了很多,晚上我披着衣服靠在阳台上,看着远处若隐若现地霓虹灯,我问自己,什么叫距离,为什么存在距离?既然心在一起,又何必谈到距离?爱过,恨过,爱恨之间,时间在一步一步隔膜我们,时间在一步一步淡化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却在我没有预料中来到。打破了距离,视线一点点开始模糊,两颗心在逼近,可怜的是,距离却在把那无形的网络罩在柔软的身躯。我想这应该是一种考验吧,心真在一起,就不怕有距离,就不会躲在一个凌空的角落,躲避那本不应该躲避的事实。
偶尔也会想起那很久以前的日子,想起一个人孤独寂寞地骑着单车穿过那单薄的青春岁月。可能真的没有可以让人忘记的东西,想忘记,就不要想起,想起,就不会忘记。而自己被回忆拉回的时候,眼神忧郁的在告诉世界,或者真的有过。“死党”杨峥曾经和我一起探讨那本不应该探讨的理论,那时候他刚和他那个分了又和、和了又分、分了再和的女朋友分手,人有点不可理喻,有点不可思议。我当时是笑谈人生,静静的享受这没有分手的日子。我们又融合在一起,为了彻底返回那个灿烂的岁月,我劝他:“在这个世界上,当你发现别无选择的时候,你必须试着去接受一种事实。”他含情默默的看我一会儿,“鲁迅爷爷说的对,‘世上大多半男人本来应该做圣贤的,结果全被女人给毁掉了。’”我*!老师让他背这段课文的时候他死活背不下来,现在一字不差!
人应该学会疗伤,当你从那围墙上摔下来的时候,难免伤痕累累,这时候最大的帮助就是自己疗伤,逃离了围城,远离了堕落的边缘,又是一个自己,又是那个活在灿烂和明媚里的生命!
流浪书生(未必)
2005年01月02日于旷野斋
离开堕落的边缘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太幼稚了,或者太天真了,总是在错过中发现自己错过了,总是在憧憬中做着未必应该做的事,总是在一个晴朗的天空默默地忧伤。有时觉得一个人生活会很好的,就像那飘落在人行道两旁的树叶,没有束缚,没有被迫,在一个可以独处的地方遥望着没有边际的天空,想着自己被风托在空气中的感觉,慢慢地享受那属于它属于心的空间。
但是,当我一个人走了一天后,才发现一个人过两个人曾经过的生活,一个人走两个人曾经走过的路,一个人坐在本属于两个人的位子是如此的让我不堪一击。或许当初不应该这样大度,把自己的生命分给另外一个人,让自己陷入那为自己而设的围城,愈陷愈深,有点窒息。
静静的穿过草地,在一个有阳光的日子里我去寻找那遗失的角落,感受着阳光依然明媚,小草依然柔弱。真的应该一点点舍弃,不应该记起那清脆的小草被折腰的声音,像留下的脚步,我没有想过让它为自己记录曾经有过的岁月,也没有想过让它成为生命中一个可以让自己伤心和无助的起点。
回头再看那地下,没有留下,我告诉自己。也许只有这样我才能让自己平静下来,才能够怀着曾经虔诚的心期待着属于自己的,而不是未必属于我的。离开草地,我努力使自己忘记我永远都不要想起的岁月,过去了终究是过去了,如果还刻意去寻求,只会让自己沉沦于回忆中,心甘情愿的接受折磨。这样的一天,我一个人把曾经不属于一个人的路走过,让记忆中残留的碎片“灰飞烟灭”,没有重新组合的将来。我苛责自己,是否应该原谅自己?
抬头,几天来阴沉的天空被这温馨的日光驱散,一股气息直往鼻孔里钻。就像五月的槐花,淡淡的,清清的,一屡香气。
后来与朋友聊天中听朋友说一句话,心若在一起,空间就不是距离,我想了很多,晚上我披着衣服靠在阳台上,看着远处若隐若现地霓虹灯,我问自己,什么叫距离,为什么存在距离?既然心在一起,又何必谈到距离?爱过,恨过,爱恨之间,时间在一步一步隔膜我们,时间在一步一步淡化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却在我没有预料中来到。打破了距离,视线一点点开始模糊,两颗心在逼近,可怜的是,距离却在把那无形的网络罩在柔软的身躯。我想这应该是一种考验吧,心真在一起,就不怕有距离,就不会躲在一个凌空的角落,躲避那本不应该躲避的事实。
偶尔也会想起那很久以前的日子,想起一个人孤独寂寞地骑着单车穿过那单薄的青春岁月。可能真的没有可以让人忘记的东西,想忘记,就不要想起,想起,就不会忘记。而自己被回忆拉回的时候,眼神忧郁的在告诉世界,或者真的有过。“死党”杨峥曾经和我一起探讨那本不应该探讨的理论,那时候他刚和他那个分了又和、和了又分、分了再和的女朋友分手,人有点不可理喻,有点不可思议。我当时是笑谈人生,静静的享受这没有分手的日子。我们又融合在一起,为了彻底返回那个灿烂的岁月,我劝他:“在这个世界上,当你发现别无选择的时候,你必须试着去接受一种事实。”他含情默默的看我一会儿,“鲁迅爷爷说的对,‘世上大多半男人本来应该做圣贤的,结果全被女人给毁掉了。’”我*!老师让他背这段课文的时候他死活背不下来,现在一字不差!
人应该学会疗伤,当你从那围墙上摔下来的时候,难免伤痕累累,这时候最大的帮助就是自己疗伤,逃离了围城,远离了堕落的边缘,又是一个自己,又是那个活在灿烂和明媚里的生命!
流浪书生(未必)
2005年01月02日于旷野斋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5/1/20 17:20:21
Post By:2005/1/20 17:2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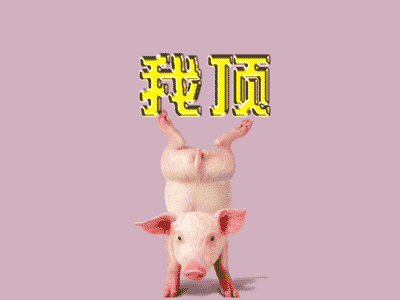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论坛我最丑
论坛我最丑
 Post By:2005/1/20 19:10:50
Post By:2005/1/20 19:10:50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5/1/21 13:32:04
Post By:2005/1/21 13:3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