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之歌剧情介绍: 你相信有吸血鬼存在吗?
天遥遥,风岧岧。教室里人潮熙攘,走廊上寂静无人,操场边热闹喧哗,车库间安然无声。眼与眼的缝隙,白云排成一长直线,轻盈漫舞,染上葱茏的青色。心情不好不坏,太过平常。
一砂是怎样的男生。头发整齐,成绩不上不下,个性不很沉稳也不太张扬。有关系很好的朋友,喜欢的女生是不爱说话的八重坚。如此而已,太过平常。
只可惜冬目景怎甘心轻易辜负了自己的画面,她那深深浅浅的黑灰色块,笔触下一钩一撇的欲说还休,好像抚到尽头都寻不着痕迹。纸页外延伸出铁锈的红,汩汩地流却悄没声息,从眉毛到发线,从脸轮廓到指关节,镜头一晃就丢失了全世界。
所以你如何能想象她去描绘校园里的羞涩和心跳,她笔下的情绪翻覆注定了不是落跑而是逃亡。如果上一秒他还在小心翼翼想靠近谁,简简单单想寻找谁,下一秒玻璃摔碎,谁都可以阅读他瞳孔中放大的惊慌。
我们是荒芜原野里徘徊的羔羊,为了寻觅出口用尽一生时间。
一砂是命运里不得挣脱的男主角,女一号却不是扶住他关心起他身体的八重坚。
社团活动只剩下无所事事的他和专心致志的她。于是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来,他说美术社比较轻松说不想回家说那里的温暖虚假不真切。
颜料被打翻,整张画被染成红色。颜料鲜红,画板鲜红,血色鲜红。苍白鲜红。
喉咙口发痒,有什么东西堵不住,眼看要割穿了皮层破茧而出。头发晕,脚底虚,以为是贫血的征兆。静一静,静一静就好。
--以为嗅到空气里悲怆的气息,以为窥得惨剧之一角,事实却远不止我所想。那些呼之欲出又不忍卒睹的真相,在这里打起了腹稿,一点点暗涌成了时涨时落的潮水,高高低低,沉沉眠眠。一砂记忆里姐姐的照片,重重捏在手上,好像还残留着指纹间的汗,许多年不褪色。反而越来越鲜明地覆盖住整个思想,遮住了大片大片的天空,压得人呼吸急促。紧迫感,太局促,仿佛呼唤着他想念,也许只是一时兴起,鬼使神差,仅凭三岁前的模糊印象,找到城市某处通往深巷的屋子。
意料之中的空无一人,整洁清净却超出想象。还有人住,还有陌生而熟悉的味道。一砂站在原地怔然,踌躇犹豫终没有向前。不注意身后出现了谜一样的少女,头发黑长,面色苍白,血管鲜红,凸凸地映出她虚弱的病颜清晰可见。少女漂亮得可怕,神色傲然,发梢飞扬无痕,高高在上俯视着他的卑微。树叶沙沙作响,急风呼呼灌耳,最后只听见一个声音,全世界的声音都聚集起来凝成同一个:
你相信有吸血鬼存在吗?
明明心里一个冷峭的不置信,偏偏顿在嘴边,成了一个隐忍渐逝的延长音。普通人都无法接受的看似荒诞的解释,一砂怎会不生怀疑。即使她对这个“家”中的一切了若指掌,即使她自称“高城千砂”是他失散多年的血亲,即使她和幼时母亲的容貌无比相似,可这一份突如其来,一砂未曾设防。
高城家,是被吸血鬼诅咒的危险人类。
尽管心里打上千万个结,盘绕成纠缠的心不在焉,还是勉强守了诺言,远离那是非之地。直到面对八重坚颤抖地昏眩,那个不愿意承认的假设才毫不留情地浮出水面,赤裸裸、活生生,失措复制很多份,惊恐卷成无限长。好奇心,不安心,一两两称到天平上不稳定,忐忑不已只为搞清自己的不确信。
千砂不以为然,无论任何时候她都不会激动或紧张。娓娓说高城世袭的“肮脏”也好,淡淡说习惯了空虚也好,也许甚至连父亲自杀或她想追随而去是也都一样没有起伏的表情,波澜不惊。就算得知一砂这个弟弟也没能逃脱宿命,也没有分毫不再孤独的欣喜。她的生命从来只为某个人忍受,如今那个人永远摆脱了她,刹那仙人掌的花朵枯萎,收拢成沙漠里跋涉天涯无处落脚的尘埃。一砂只是刚认识的路人,虽然有相同的不幸,却没有同样的寂寞。
水无濑和往常一样替她复诊,他问她为什么要告诉一砂。就算是弟弟,却没有丁点感情,我没有义务和他们一样心惊胆战守护他的面具。我没想害他,但他有知道的权利。
明白吗,我们是世上仅剩的吸血鬼,不必妄想逃脱,前人早设尽各法。
千砂把药递给一砂,发病的话就吃这个吧。水无濑看在眼里,质问道,你在重复你父亲做或的事吗?
也许。那个被千砂铭记了一生的男人,到结束也没给她救赎的机会。涉足高城家的旋涡,带给他的,只有一双儿女和伤痕累累的身体。送走了儿子,女儿就成了最重要的牵挂,最后还是不堪重负撒手离去。
也许是在报复。报复父亲的背弃,所以苟延残喘咬牙活下去;报复他给的爱和恨,所以连带这份喜憎一并保存。报复他给的血,可以渐渐和一砂重叠的容貌,报复他可以给自己关爱却不是她的爱人。
千砂有点迷惘。不想重蹈父亲的覆辙,却不知不觉犯下相同的错误。平躺在塌上,看见自己的头发凌乱拂过鼻尖,看见自己的掌纹交错不辨方向,看见风铃带来流淌的橙红,弥漫成整个天际的恍惚。
可是,总有什么不对劲。一定有什么不对劲。
药贴在一砂的口袋,和着走路的节奏上下颠簸,就在稍稍放心的间歇,瞬时被一股莫名的冲动卡住了脖子。呼吸狭促,那么清楚地听见药片撞上瓶底瓶壁的旋律,难受一度扩张,顶在舌尖上摇摇欲坠。意志翻滚,决心搏斗,无论如何都不愿妥协,一旦退让一旦服输叫害怕占了上风,从此就只能伏在欲望狰狞的面孔下卑躬屈膝。
我说过了,抵抗是无效的。
千砂不是一砂的救星,他的谁都不是。她挡住他额前的明艳和灼热,用刀子划开了手臂。
喝吧。
我和你不是姐与弟的关系,而是血脉与骨肉的栓连。
所有的视线都被蝴蝶的翅膀扑住,所有的听觉都归纳为同一种频率:
你相信有吸血鬼存在吗?
神经忠实地把敏锐的触点散布,仿佛还可以看见在浅浅的皮层下它的跃动。世界被涂满黑白红,鬼魅的画面。梦境里尚幼小的姐姐咬断猫的喉管,梦境里八重坚浑身血渍,好像凝固了,怎还有窸窸窣窣的回响--是恐慌在门前来回踱步的尾音。
八重坚周围方圆的寸地,是一砂难以跨入的禁区,伸手不可及。言语和行为都禁锢在遥远以外的天地,不声张,不喘息。不再相互对视不再无谓联系,从此相安无事。
如果全都不在意。
但是无法不挂心。
疑惑抓住了自由的脚踝,失望到处走,漫无目的地走。一砂半身的素描靠在墙角,美术室里还残着最后一分期待,可是难过不解越堆越高再不能忍耐。
一砂你撒谎了对不对,否则你凝视我的眼神怎会那么无辜。请告诉我,请回答我,再巨大的残忍也不及你说讨厌我那般伤得我体无完肤。
八重坚的困惑终于释放成对一砂的追赶,任凭一砂怎样哀求她离开仍没有丝毫动摇。现实和梦境一幕幕闪烁回放,倒空了药依然抑制不住。越来越强烈的是不能伤害八重坚的愿望,有刀只能往自己身上割,舌尖舔上血液流过处,疼痛刺眼。一次两次,从她的退却到鼓起勇气,若在从前,一砂会是怎样高兴。
然而假设毫无意义。
一砂被送往医院,收养他的江田夫妇和千砂在病房相见,八重坚站在一旁装作对事情全不知情,水无濑以“中暑”为借口含糊搪塞过去。千砂正式向一砂的养父母提出要和他一起住。和世上唯一的亲人相依为命,照顾我这个拖累他的姐姐,很正常。一砂沉默无言,低下头把唇齿的牵动一一掩埋,一秒种的对视都可能泄露。
压在舌下的秘密,不能把身边的人卷进去,就此撤离。所以即使口不对心纵然心口滴血,还是狠下心掷出谎言,铿锵落地,没有弹起的回声。
从此古老的宅子里有两个人了。似乎父亲的影子依旧伸向各个角落挥之不去,似乎回头望去还可以全力拥抱。可是哪里都找不见,找得见的只有心里坑坑洼洼的伤痕,丑陋的疤铺张开去;找得见的只有施舍般的温暖和反反复复的短叹,急刹车,重演很多次。
竭力斩断与周遭人事的关系,生活的范围束成单调的格子,固定在屋子里混沌的空气。不愿意,却无可奈何;想脱离,却无处可逃。千砂一身和服,面色白如纸,手指透明如玉,嘴唇上下两片交叠,妖艳如血。
--我不能成为你活下去的必须吗?
--你能成为我活下去的理由吗?
可以吗。声音虚空,在碧落划过的轨迹,不留下供人捕捉的契机。声音清冷,匆匆拍上面颊,容忍不下炽烈的温度。转几弯,没交点,有落差。
对千砂的责任心仿佛骤然沉重,并非血缘的纠结,而在不加察觉的挥袖抚眉间演化成顺理成章。不分离,哪怕一再背弃旁人的千呼万唤。
千砂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不发病时也随时可能晕倒。药对心脏的负荷太大,已经到了极限。水无濑不再给她开药,只有拜托一砂。他是唯一有可能不被千砂拒绝的人,水无濑想成为那样的人,可她从未给他机会。
一砂慢慢习惯控制自己的身体,试着回校上课,就算只是默默行走至少还可以听闻人声。放学后晚上独自看星星,千砂已被带去横滨,望断天涯终不能穿。
水无濑的无奈昭然若显。他的人生自与千砂相遇后就不再完整。起初把她当成孤僻的妹妹一再关心,后来在某一个阳光潋滟的下午,轻易被七岁的她一个轻蔑的眼神征服。那一日在左眉留下的伤疤长久不褪,誓成他爱着的最可宝贵的证据。他为她当上医生,在她初中毕业要带她私奔。到现在还后悔,当初怎么不狠心带她走,否则就不会落得今天无可挽回的局面。
火车几万里,地铁多少米。千砂从病房出走,失去意识前最后吐露的字眼就是要回东京。
不久后她偷了药只身返回,水无濑明白他无权也无力阻拦。
没有千砂的日子,时间流逝如水一般细长。他带着她给的毒药穿梭于学校,好像只有如此才有足够的勇气面对没有她的孤寂。
楼梯上打翻一整瓶红墨水,眼睁睁看鲜红流淌一地。久违了的一次犯病,是八重坚主动把脖子凑上他的齿尖。两点鲜明的齿印,耳边血流的声音,成全她等待的宽慰。但是一砂心里一个明晰而静谧的轻响烙下:自己想要的,并不是八重坚的血。
只有千砂。
高城医院的旧护士风见找到那里询问医生的死因,动机天真而单纯。她从墓地旧家一直查到医院里嗜血症的资料,想起被辞退前医生说的种种,想起他身上从不揭掉的膏药,从而推想他那个身体虚弱的女儿所患的古怪的疾病。千砂找上她,让她别再插手。你看,爸爸本是个外人,执意要分担母亲的痛苦,最后落到非死不能解脱。
与“高城”有牵连的人都不得善终,所以请赶紧放手,一旦晚了就万劫不复。那个把自己女儿当作妻子替代品的古板男人,有什么好?
是啊,有什么好。没有任何的好为何还苦苦记得,死也不得忘。
千砂在她的面前旧疾发作,颤抖着把药倒入口中。你没有见过真正发狂的样子,这种真实不该触碰。我们是生来带牙的羊,而非披着羊皮的狼。风见脑子里重重敲下医生的侧影,和眼前的场景堪堪撞击,早有准备依然惊诧勉力镇定。
你相信有吸血鬼存在吗?
并无知觉之下已经习惯相互扶持彼此信赖,不介意关于母亲的沉痛回忆,不留心一个个季节的过去。千砂的病情日益恶化,靠在一砂怀里叫他不敢用力。
冬天,雪花纷飞落在地面,把一切盖成白色。千砂的面容苍白,千砂的和服鲜红。苍白如雪,鲜红如血。苍白鲜红。
我爱你。
声音浮浮沉沉,起起落落,在心口堆起千层的雪。声音蛰伏在喉下零点一厘米,终于潜埋不住变成了一个释然的爆破,风舒云卷在苍穹回荡千万遍。声音飞久了累了,在枝间一个停顿,就化作长虹摇光曳影几世纪,缠连不退。
对不起。我爱你。
不是把你当成我的姐或弟,也不是把你当成谁的替代。而是在广袤的往昔和辽阔的将来,在没有父亲母亲的溪流山涧与你相遇。
如果可以我愿意一辈子守在你身边,可如果不行就只有尽我的绵薄努力做些什么。你的血混合着我的血,难道不是最重要的不能割舍吗?我死了以后,一砂就能和八重坚在一起了,你不是很喜欢她吗?我想向她道歉,跟她借了你那么久……
千砂你记得你给我的毒药吗,我一直带着它,有它在我才能感觉踏实,因为这样我才敢想象你的离去。要是你死了,我绝对会吞下它,因为--只有千砂,才是我生的原因。
千砂闭上眼睛没再睁开,一砂握紧她的五指没有松开。他们的羁绊从出生开始,从他们的重逢开始,从她给他血开始,直到死也不会停止。这一晚谁也没有睡着,人们辗转反侧总有什么疙瘩着太揪心。再然后春天来了,千砂的坟头花香鸟语,里面是没有灵魂的冰凉;一砂在病房里一日日恢复,八重坚天天前去探望。无以言喻的悲伤和无处泣诉的凄哀,整日盘旋。忘却在思念的边际日夜生长,迅速连接起绵延的荒芜。日子就这么一格一格放过,寻不找终点。
一砂失去一年来的记忆,改了姓转了校,也失了嗜血的表征。
如果可以瞒过全世界。
但是空白没法不去填。
可以改掉姓氏,可以转读他校,可以对“姐姐”绝口不提,可以收起报纸杂志关掉广播电视。可一年的光阴不会流尽没有尾痕,一年的沧桑不会就此打磨光洁,一砂心里的缺口终会日渐扩大,只是他听不见也看不到,无边无垠的空旷也只是错觉平日太过匆忙。然后对着八重坚微笑,头发贴住额头,眼睫毛遮住光线,没有其它,太过平常。而与千砂之间最无法放弃的珍贵,抬头不见,低头也不见。
谁是荒野里徘徊的最后一只羔羊,就当作忘记了不再提。
也许很久以后有人不经意提起,就好像吃饱饭睡足觉没事干一样随口问起。一不小心也触目惊心。
你相信有吸血鬼存在吗?
那个人猛一个踉跄,似乎还抓了抓脑皮漫不经心地回答:那种事……谁信啊?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8-2 10:12:21编辑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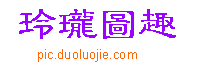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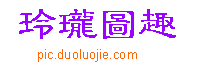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漫步太空の人
漫步太空の人
 Post By:2006/8/1 17:06:00
Post By:2006/8/1 17:06:00

 在人类的圈子里,每天扮演着各类的角色,恰比演艺圈的巨星,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在人类的圈子里,每天扮演着各类的角色,恰比演艺圈的巨星,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漫步太空の人
漫步太空の人
 Post By:2006/8/1 17:22:00
Post By:2006/8/1 17:22:00

 在人类的圈子里,每天扮演着各类的角色,恰比演艺圈的巨星,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在人类的圈子里,每天扮演着各类的角色,恰比演艺圈的巨星,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我丢了一只猫
我丢了一只猫
 Post By:2006/8/2 9:35:00
Post By:2006/8/2 9:3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