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我们坐在一楼通往二楼的室外台阶上,一楼是商店,比普通的房层高,楼道的感应灯,没有声响,于是四周漆黑一片。楼外就是马路,因为午夜偶尔才有车经过,夜深路旷,出租车开得风驰电策,呼呼的一阵响。灯亮了。一分钟里我可以看清他的脸部轮廓,半闭着的眼睛在无框镜架,说有更似无的遮挡下疲倦不堪。他累了,我却因为坐在他旁边兴奋不已,像精神抖擞的黑猫,炯炯着双眸。灯灭了。我含住他搁在我肩上的手指,双唇微微用力,舌尖在他的指面上轻轻地画圈,我知道那种感觉会酥酥痒痒,有时还能牵动着背部神经微微一颤。我经常这样对待自己,在食完巧克力后吸吮自己的手指。我体贴他的感觉,所以常拿自己试验。我甚至羡慕能替他体检的医生,悔恨怎么不曾学过医科,然后就能体会是怎样的骨骼造就他,可以用手细细地摸索……摸索……他微微一颤。我乘机轻轻转下他手指上的戒指。我说:送给我。
他说:不可以。
我们靠在二楼某家人家铁门边亲吻。我喜欢他的高度,两相适合,刚刚好好,可以双手环住他的颈项,怎样被他抱紧都很舒适的姿势,我的左手在他颈后的发根部轻轻摩挲。他穿着小圆领的灰色毛衣,衣服内蕴藏着他的体温,混合着烟味。他越逼越紧,好像被我刚才挑弄手指的舌尖诱惑到。我应对他,我总是越慌张时越有条不紊的人,就像考试前最后几天才开始冷静复习。但我害怕考试,因为不知道考卷是否就是我预习到的内容。我害怕他,我愈被他揽紧越害怕。可当他安静时,我又忍不住诱惑。好像引了山火又不愿负责任。这时有人下晚班上楼梯,楼道的灯猛然亮了,我牵着他的手飞快地向三楼跑。来人在二楼停下,开门进屋。灯灭。我们在黑暗中相视,我想笑,他却继续想拥紧我。我甩开他的手往四楼走。他渐渐恢复沉默,跟在我身后。四楼,死寂。我拿出那枚戒指,在他眼前晃动,我说:送给我。
他一把抢过。他说:不可以。
如果送给我。你要什么都可以!我开始和戒指较上劲。
回家睡觉吧。我累了。
一切开始变糟。我在五楼的过道里哭。他开始抽烟。没有一句安慰的话。我哭到他烟抽完,他走到我面前,狠狠踩熄烟蒂,灯亮了。他将戒指从手指上褪下递给我,他说:给你。
我却突然对它丧失兴趣。也没有擦眼泪,只是忽然用那种无所谓的表情看着他,然后绕开他走上楼梯。
六楼,我用钥匙开603的房门。连句晚安或再见也没有说,我直接进入房间,关上房门后,我静静地靠在门上听他停顿一阵后,用钥匙打开602的房门,然后进屋。开灯。关灯。
凌晨3:47.我拨通他的手机。我说:顾青。我睡不着。陪陪我吧。
他喉咙沙哑,好像着了凉。声音十分困倦,我听得出他努力按耐着被吵醒的怒意与无奈。他说:你想聊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回答,好像有戏弄人的意思,但我没有说谎。我真的不知道。
沉默……
他想了想,然后说:我给你唱歌吧。
我说:好。我喜欢听你唱歌。
于是他唱刘德华的《你是我的女人》。我喜欢国文歌词,但他唱的却是粤语歌词,很多句我都听不懂。以致于我感动地想哭,却流不出眼泪。六楼,我想翻过两家的阳台到他身边去。并且我敢这样做。可是我害怕,不因为六层的高度。而是怕入不敷出……
电话突然挂机,歌还没有唱完。检查电话,发现是我自己激动到将电话线拉过头。我没有再打过去,他也没有再打过来。
我睁大双眼。一直等。最后。没用的睡着了。
梦见他在梦里打我。恶狠狠的一个耳光,我捂着脸不声不响走出去。想不通。他怎么舍得。然后醒来。时间将近中午。整理床铺时闷闷不乐。穿过客厅去梳洗时,顾青的妈妈正坐在沙发上和我妈聊天。她们经常互相窜门,看似热情的话语其实空洞无聊,还有互相攀比炫耀的情愫。我叫了声阿姨,她说诶。其实彼此一点好感也没有。
她说:我家顾青周末要带女朋友回家了。
我妈用同样热烈的语气回答:是伐……要当婆婆来……
她装出一半快乐一半又不在乎的口吻说:其实我也不怎么赞成的,我家青青和你家苏一样大呀,年纪嘎轻,小姑娘都还没急着嫁。他倒急着娶来。养儿子不好,废钱……
我对着镜子刷牙,洗脸,面无表情。水蒸汽在镜子上起了一层雾,我用手指在那上面画一个小脸,水气凝结下滑,小脸开始流泪。我却依然面无表情。
听见我妈开始应答:苏周末也刚好要去相亲呀,她姐姐给介绍的,听说家里很有钱的。本人又开公司,我让苏去看看,年纪还小,不急,好挑挑拣拣……
听到这里。我走向厨房准备吃饭。结果什么都没有煮,只有方便面。
我说:妈,饭呢?
她斩钉截铁地说:没有。满是话语被打断的不高兴。
我说:那怎么办。声音只有自己听见。那怎么办。一句没什么对应的回答。好像在说另外一件事。
我回到房间盯着小闹钟发呆。想他早上都做了些什么,中午在哪里吃饭,晚上是否要加班,他今天穿了什么?灰色毛衣是否换下,裤子昨天在台阶上坐脏了……他怎么舍得在梦里打我……
好像即使在梦中也是不能原谅的事情。是否在晚上打电话给他质问?其实自己心里很清楚,8:00以后他的电话永远是占线,上两个小时网打游戏,然后下线给女友打电话。一周工作日有五天,天天通一小时电话,一周双休日两天,见一次到两次。整整两年,执着成习惯……
6:00到12:00我开始上班,滨江的HOT DOT咖啡座,我扎上暗青色侍者裙,彬彬有礼的招呼每位客人。电脑递单时,我想念他捻烟的手指,送咖啡时,想念他看着电脑屏幕的那双眼睛,说欢迎再来时,想念他正在同女友电话的嘴唇……
一周有七天。我们没有什么理由靠近。
[二]
那男人坐在我的面前。像受人控制的水阀。沉默一阵打腹稿,然后滔滔不绝的说完。再沉默一阵打腹稿。唾沫喷得极远,一颗溅入我的奶茶,他竟毫无知觉,问我怎么点了东西不喝。我常侧脸去看窗外的立交桥,避风塘开在这样的路段,毫无一点生趣。有一桌男人在角落里打了通宵的牌。店员在空空的茶室内吃潦草的午餐。忽然想起,早上经过顾青家时,他爸爸正在煮酱鸭,香味浓郁,弥漫整整三层楼面。算算时间,他们应该准备开饭了。桌面上菜肴丰盛,四人端坐,那女孩吃相斯文,总是不常举筷,令人怜惜的安静。那个家庭所喜欢的一个媳妇模子正是如此。我想着这些,然后对面前那个男人聊一种叫做鬼斩的游戏机。站在大屏幕前用刀乱挥,很真实的搏杀感。
我猜不出当时自己面部的表情。奶茶也始终没有捧起来喝。
那男人说既然坐着没意思,不如出去走走。我站起身,他比我矮。不清楚是否怕站在我身边尴尬,所以他刻意不停下来等我,保持一前一后的距离,我在他身后,看着他那条过长,有些空落落的裤子。
我们在商业街上毫无目的地踱。却都没有心情逛商店。他聊他出国时的经历,我在考虑怎样逃跑。一小时后,我借口说着凉不舒服回到家。
隔壁还在欢聚,一家人唱卡拉OK,顾青父母合唱完一段黄梅戏后。一个温柔的女孩子声音,羞涩的唱起《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我的世界万籁俱静,我几乎抑止住自己的呼吸,怔怔地坐在床上安静地听。这是我第一次弄清他每晚在接听一个怎样声音的电话。怎样的声音让他着迷……一曲结束,热烈的掌声。
接着,顾青与她双双对唱《相思风雨中》。几句过场,又是掌声。
我打开音响。将郭富城的《最激帝国》放到最响。震耳欲聋。直到隔壁音乐停止。我才关掉音响。整整一分钟,气氛凝固。
缓缓地,音乐又起。他的声音。刘德华的《练习》。唱到空气像水一样在我面颊溶解。我走上阳台,看见他那件灰色圆领的毛衣晒在外面。我想他怎么不唱郭富城的《唯一色彩》呢,多讨女友欢心的歌。忽然觉得大无所谓,拿起零钱袋关门出去。
独自在大商场内的游艺部玩魔斩。像拿菜刀一样拿着忍者刀乱砍,引来许多人围观。猛砍,猛砍,手酸到握不紧一瓶矿泉水。
夜里10:00.猛的电话铃声,我跑去接,几乎被自己绊到。却是姐姐的电话。她问我对那男人感觉怎样。我回答根本没感觉。结果她说:结婚就是这个人家里有钱,大环境好,对你也不错,钱肯给你用,感情算什么,又不能当饭吃,时间一长,什么感情都没有了,你先别斩钉截铁否定他。你再出去交往看看,说不定就有感觉了……
我很想笑,不知道同那男人的感情究竟该怎样培养。我说:那不是骗人吗?
姐姐说:什么叫骗人!你干嘛不给自己一个机会?也给别人一个机会。
她的劝说真是落力极了。恨不得明天最好就结婚的热情。
我挂上电话。在床上翻转身体,双手酸痛。心里却没有什么烦恼,好像都在玩魔斩时发泄掉一样。又是电话,我懒得接,妈妈在客厅接了大声叫我。我拿起话筒,愤愤地说喂。
他问我:今天怎么样?
没怎么样。我知道他问的是相亲,他妈妈肯定有告诉他了。可这问题实在没什么好回答。
沉默……
我忽然用很快乐的口气说话。知道嘛,有天我恶梦梦见你了。
恶梦?不是梦见我拿刀砍人吧!
才不是。梦见你打我了。恶狠狠的一个耳光。
啊?
哈哈!我要找张符给你贴一下。以后绝对不可以在梦里打我!
呵呵。他微笑,若有似无。
好。困了,累了,晚觉。晚安,好梦,BB.我一口气说完一串话,理由,目的,祝福,告别……好像我能做的事其实很简单,根本几个词就可以说完。所以就快点说完,然后没有空隙,没有余地的说再见。
挂电话。我说服自己没什么好再聊的。说不定聊到最后,还要问噪音干扰道歉。翻转身体,我真的很累。想睡觉。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
关灯。四周黑暗。剩我一人蜷缩着害怕。
又是恶梦。水里一条凶猛的大鱼追赶我,不能呼吸还要逃跑。脊背神经一阵麻痹。直到第二天晚上在HOT DOT端着盘子想起,依然觉得背部僵直。我递给某个德国人一杯柠檬净水,彼此用生硬的英语交谈。他穿着灰色的圆领毛衣,因为这个,整晚我只对他有许多笑容。或许我笑的真的太殷勤,他离去时给了我小费夹着他的名片,并且问我要电话号码。我随手抄了手机号码给他,半小时后,我猛然想起,留给他的电话号码是顾青的。于是我俯在吧台里笑。拿出吸油面纸吸去眼泪。
同事问:你怎么了。
我说:不当心喝水呛到了。
她好心的拍我的后背。那根神经又开始发麻。
12点整下班。一个小时的自行车车程。起风。我飞快的骑着,面部与手脚冰凉。情侣躲在阴暗处亲吻,发廊里的女人在门口张望,24小时的便利店,这些场面一晃就过去了。路面修整,吊车,推土机,程建工人在挖土,大多是外地民工,看见子夜有女孩子骑车过去,拼命的吹着口哨。轰鸣的机器劳作声与刺耳尖厉的口哨声夹杂在一起。都市的夜晚像痴呆老人的睡眠,半亮不亮的天空,很轻的睡意,鼾声,口水,梦语……
我去车库停好车。并不愿回家,坐在台阶上抽烟。新买的卡通钱袋很大,索性做了烟包,香烟与打火机容纳在内,精致又不易被发现。我将香烟拿在手里,红光一点,快速旋转,无数个红色的光圈。好似熏香,沾染上他的气息。
我从来都不知道你究竟在想些什么?有人在我身后说话。灯亮,我坐在他的影子中。
什么也没有想。
我扔掉香烟,站起身拍拍裤子上的灰。与他擦肩而过上楼。听见他很重的一声呼吸,然后抓住我的手。很疼。他果然舍得用力。没有挣扎,我的力量在他面前分崩瓦解。他说:告诉我,你究竟想要些什么?
我想着你有什么资格来问我。结果沉默。我用双手从背后环绕住他,依靠在那里,好像拥抱倒比言语更实际。不需要坦白,不需要澄清,只要紧紧地偎贴在一起。嘴唇在他的脸旁,他侧过脸就能吻到。他的手覆在我手上,十指交握。然而距离越近,我们越不肯说实话。
他牵着我的手上楼。我说:顾青。你头发太长了,可以剪了。
他说:哦。
[三]
顾青和女朋友外出旅游了。他离开我整整两天零7个小时。完全感觉不到他与我在同一个城市。这些时间里,我第一次留意HOT DOT的新店长。NEO.27岁,来滨江店第三周。不太爱说话,有时候我们玩笑开过头也只是皱起眉头,似怒非怒的说:别闹。他看起来很好相处,也不曾见他大声训斥过谁,但我们都害怕他。觉得他城府很深,各人好自为之,每次轮到他值班,大家行为都相当收敛。
我经常绕开他的眼光做事,因为懒得给上司讨好的笑容。敷衍很累,当然能省则省。他在吧台里监磨咖啡时,我正在清洗几只杯子,侧脸看了他一眼。发现女店员门背后议论他像混血儿真有些道理。NEO的五官很欧化,浓密的头发,眉毛与长睫,因为轻度近视,喜欢微眯着眼睛,像部电影的名字《花眼》。更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画家。
我借口清理垃圾,躲在杂物间里抽烟,实质也并不抽,依旧点燃了拿在黑暗中晃。两天零七个小时,他们该发生的都发生了。譬若胶着后还能有怎样的见缝插针。
NEO猛地打开房门,我愣怔着与他对望。
他说:嗯?什么事情想不开?
表情很可爱,好像女生吸烟,就是因为心里不开心。而不是什么烟瘾。其实他自己烟瘾很重。后来我才知道,这间杂物间原来是他经常躲着抽烟的地方。我擅闯了禁地。
我说:你想听?
他想了想后回答:你相信我?
我笑了。
那晚整个HOT DOT的人都离开后,我们开了两瓶朗姆在店里聊天至到凌晨四点。我聊到那次相亲,家人的软磨硬泡,还有那个裤腿过长的男人。但是只字也没有提到顾青。好像从来就不曾有过此人的存在,好像我的烦恼全来自相亲,和他没有一点关系。
他说:这是你终身的幸福。自己立场要坚定。我绝对不同意。
我说:你的肩膀能借我枕一下吗?
他披着外套,衣服感觉很厚,但是柔软,身上也有烟味混合着。闭上眼睛,觉得他异常熟悉,好像从来都是这样亲近的相处。他像收留一只迷失的小猫一样包容着我。凌晨四点,我们友好的说再见。各自回家。
然而第三天。我们再见面时,他闪躲我第一眼注视的目光。然后我也不再注视他。我想,不过就是这样。两个人擦肩而过,互视一眼,看出对方有些伤痛。接着离开彼此的视线,影子,越走越远。聪明人不会将自己牵扯到别人的伤痛里去。我想起他那句,你相信我?
其实。我只会隐瞒,但我不会说谎。我想说。是的。我相信。但是你相不相信我?
顾青回家后来我家送了一些土特产。我没有遇见他,只是在桌上看见许多小胡桃。还有一把夹碎胡桃的小钳子。我在深夜将胡桃一颗一颗砸开,动静很大,以致于电话响了半天,我还在残酷的敲击着一颗胡桃,笑容有些神经质的狰狞。
他说:你干什么呢?
我反应有些迟钝,我说:啊?
我在阳台上。你出来。
整整两天零七个小时。我看见他。修剪到很短的头发,他站在阳台上抽烟。我则穿着睡衣,拿着一小塑料的核桃仁掷给他。
他说:干什么!买给你吃的。
没人搭理。半晌后。他说:明天我们公司同事在KTV唱歌,一起来吧。
我没有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请错人了吧?
呵呵……很久没一起唱歌了……来吧。明天你换下午的班,我下班后借经理的车过来接你。就这样定了。
依然没人搭理。我不太敢回答,怕一出声音,结果醒来发现自己在做梦。
他只是微笑,好像不在乎我让他自言自语的尴尬,扔掉烟蒂,说晚安后转身回房间。
我或许从很久以前就在开始同他玩我们都是木头人的游戏。我像沉溺在深海,却还要自行忍住呼吸。起身落身,深海珊瑚像街市霓虹,朦胧在藏青色水中的光彩,暗暗地有些热量。我想我们忍耐吧,反正有许多时间可以残酷地对战,我不相信如同你也不相信。仅此……而已……
[四]
凌晨四点。我哭着醒来,睁开眼睛,天花板上空无一物。我开始想今晚要不要带他送给我的圆形耳钉。要不要乖一点,但又似乎不是我的责任。他怎样向同事介绍我?想着想着,黑暗成了满屋的光线。
HOT DOT当天下午的生意出奇的清淡。一个下午漫长地让人无从打发。我几乎站着就要打瞌睡。NEO在一旁盘点着吧台存货,忽然递给我一卷糖。他说,怎么没睡好吗?还要换午班。晚上出去玩?
我狡猾地微笑。
结果当晚。我的表现如同这个笑容一样诡异莫测。关灯,快歌,接受他所有同事乘他在KTV包房外的挑衅,含着一片柠檬,同他们将一瓶瓶克罗娜一饮倒底,几乎是蛮干。他从屋外进来,发现气氛异常。我们一起笑着挥手说没事,没事。像一同犯了错误的小兵面对挑剔的将军。然后找借口支他出去,一屋子的人继续喝。他怎么能有这样一群疯狂地同事,让人想像不出平时里是怎样一个一本正经、严肃的部门机构。胡闹就会有人响应,难道黑夜引诱人爆发潜意识的冲动?天知道……天才会知道……
当我躺在汽车后座上时,并不清楚他正有着怎样的表情。背后醉眼看他,平静、沉默一如既往。好像他有在包房里训斥谁来着,反正不会是我。当时我已经醉倒在不知谁的怀里。那人晚饭吃了茄汁,衣服上滴到,有酸甜的味道。
我说:不要,别听游鸿明的《一天一万年》,做作!关掉!
没人理我。
我说:为什么不理我!为什么不同我说话!
依旧没人理我。
我开始哭,没有声音的落泪。车子停下。他点烟,抽烟,然后熄灭。
他说:为什么你就不能乖一点。为什么你就不能安安静静的!
换作我不加理睬。
说话!他语气加重。
不要吵。我翻转过身,半张脸下湿成一片。然而我用醉着的声音敷衍。午夜适合安静,适合睡眠,不适合吵架,不适合分裂……他下车,关车门。走到后面,打开车门,蜷起我的双脚,坐在我身边。一系列动作,简单直接,甚至有些叫人害怕。我蜷缩起来,像刺猬受到袭击时卷起身体。但我没有刺,抵挡不住任何攻击。我努力用小动作擦眼泪,可这一切全都在落在他眼底。他拉我的双手让我坐起来,正面相对,我全然湿掉的面容。遗落掉一只的小圆耳钉。于是我也得已看见他同样湿了的眼睛。我强忍住不被那泪水感动,装出贪玩,小心翼翼摘下那副无框眼镜,它从来与他形影不离,有时甚至嫉妒它可以总在他面旁,被他小心呵护。我摘下它然后给自己带上。我说:怎么看不清啊,带着头晕……他笑了,说:你有近视吗?胡闹。
我说哦。半个音节。嘴唇被封住,失去声音。那双唇湿湿地往来。面颊凉滑,紧贴时可以体会到初生的胡须,来回摩挲,用力时我则会被触痛。然而没有人管我,连我也索性放弃了自己。一个与疼痛紧密关联的游戏,起初玩时就像喝了兴奋剂与镇定剂综合交错的药水,不是尽量避免自己疼痛,也不是尽量让对方疼痛。而是怎样都会受伤,所以干脆蒙上眼睛承受。他修长的手指游走在哪里,伴随着猛烈的呼吸。我还能被酒精刺激到何种状况,一切都像亢奋至疯狂的试验。自虐。毁灭……
如同神话中的角色,抽下头顶高悬的剑然后刺入自己的身体。
我用手指勾勒他面部的轮廓,曲线柔和,然后向下,像艘环绕地球的航船,在金黄色的海洋上漂浮游走,他的眼睛,鼻梁,嘴唇,喉结,无处不到。直至胸膛。终于他被我弄醒。我还想装睡,却被揭穿。
在某家宾馆,某个陌生的房间里,某张床承载着沦陷。我想用什么在上面能留下痕迹。记住这个地方,否则,我怕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证明,我们曾有过勇气,用身体面对并回应过彼此。好在身体无法说谎,否则我怕真的再没有什么可以印证了……
动作。停顿。发生些言语。聊到今天的天气,却没人去碰触未来怎样这个敏感的话题。依旧像较劲一样装作不在乎。身体被思想主宰,思想指示语言。语言于是有权选择隐瞒或说谎。我不会说谎,我只会隐瞒。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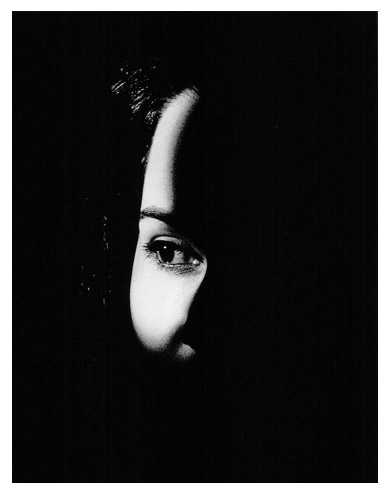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3/8/9 12:49:00
Post By:2003/8/9 12:49:00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名人堂成员
名人堂成员
 Post By:2003/8/9 13:00:00
Post By:2003/8/9 13:00:00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名人堂成员
名人堂成员
 Post By:2003/8/9 13:01:00
Post By:2003/8/9 13:0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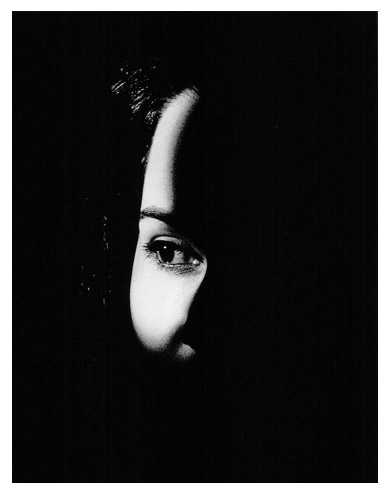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3/8/9 20:49:00
Post By:2003/8/9 20:49:00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名人堂成员
名人堂成员
 Post By:2003/8/10 15:11:00
Post By:2003/8/10 15:1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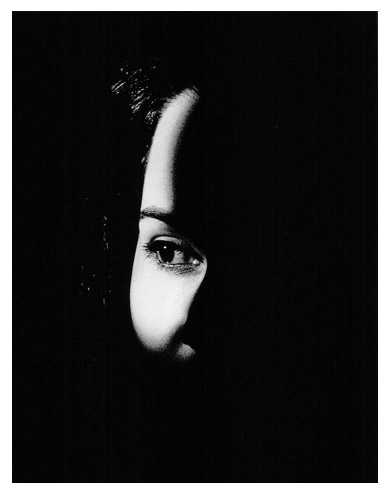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3/8/10 19:48:00
Post By:2003/8/10 19:48:00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名人堂成员
名人堂成员
 Post By:2003/8/10 21:10:00
Post By:2003/8/10 21:10:00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名人堂成员
名人堂成员
 Post By:2003/8/13 21:03:00
Post By:2003/8/13 21:0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