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农业篇
春天来了,天气变暖和了,人们象惊蛰的虫子一样陆续从树上下到地面上来,一个个形容枯槁,奄奄一息。但人们见面总要寒暄几句:啊哈,你又胖了;哎呀,你气色好得跟刚出壳的鸡崽一样。借此来鼓舞彼此的士气。三两句善意的安慰往往能拯救一个绝望的心灵。在那困难的时期,一定要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人可以被野兽杀死,但一定不能自己杀死自己。
有人开始在解冻的土地里播下种子。有人播下的是西瓜种,秋天的时候收获了无数的西瓜;有人播下的是大豆种,收获了好几麻袋豆子;但也有的同志种下了蒺藜种,收获了一地的刺儿。原始的农业就在这不断摸索中蓬勃发展起来。
六、畜牧篇
太阳逐渐变得又大又亮,烤化了田野中的积雪,烤融了小河中的坚冰。大地吸足了水分,开始孕育生命,田野中大片大片地变绿,小树儿也在枝头使劲地抽出嫩芽。
动物中先是昆虫们探头探脑地出来了,其他动物也象在冬天埋伏好了,专等春暖花开的时候突然蹦达出来吓人一跳。
我们都被吓住了,仿佛是一夜工夫万迹踪灭的田野又变得热闹沸腾起来。
任何生灵都是顽强的,只要有适当的环境,它就能生生不息地繁衍下去。当一种生物开始过分地要求其生存环境时,也就是离它灭绝之期不远了。
那个冬天的寒冷和饥饿在任何人心中都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也让人脑子的利用率空前地提高起来,有的人开始未雨绸缪,他到田野中捉一些野兽回来蓄养。
刚开始,人们都热衷养老鼠。一是老鼠除了石头和屎,什么都吃,好养活;二是老鼠繁殖飞快,一年能下好几窝,一窝能有十几个;三是老鼠肉又嫩又香,色、香、味俱全。
于是我们每个人都养了一大群老鼠,我们常到田野中去放老鼠,看到自己的老鼠被放牧得滚瓜溜圆,象一个个会走路的肉一样,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色彩。
那时候,老鼠比较老实,也训练有素,排着整齐的队伍有条不紊地吃草,放养起来丝毫不费任何力气。
但,这种好状况仅仅持续到那年的秋天。
秋天的时候,地里的庄稼成熟了。在一个清冷的早晨,人们养的老鼠全部失踪了。后来,人们在庄稼地里发现了他们,那些混蛋以风卷残云之势吃光了所有的庄稼,并一哄而散,躲到人们找不到的田野的角角落落,预备第二年的秋天卷土重来。
我们傻眼了,面面相觑,彼此都从对方的眼睛中看到了自己的愚蠢,我们这些白痴在地头呆了好久,最后都神情落落地离开了。
那天夜晚,有人在黑夜中高唱:“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声音哽咽,划破了浓重的静夜,一夜不绝。
后来,就出现了一条不明文的约定俗成的准则——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可见人们让那群耗子伤害得有多深。
这种背信弃义的东西,人类就一直没有驯服过,老鼠的天性中就具有了汉奸特务的性质,也许这话错了,应是汉奸特务天生就具有了老鼠的性质。
无疑,第一次的畜牧业的尝试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但也让人们掌握了大量的宝贵的经验。
后来,我们中有些具有锲而不舍精神的同志开始养兔子,他大获成功,成了养兔专业户;有的抓了几头野猪来养,养了几年后,头大*小的野猪走样了,变得*大头小,肉就更多了,他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还有的人养羊,养牛,养驴,养马,也都成功了。
在成功喜悦的激励下,有位异想天开的同志开始在家畜繁殖上做研究。
他让马跟驴杂交,那匹母马后来下了个杂种,一出生就“罗儿、罗儿”地叫,他给它取名叫“骡子”。
他让豺狗和豺狼杂交,生下一条比较温顺且特别忠诚的东西,他让那条杂种看家护院,并取名叫“狼狗”。
他让老虎跟猫头鹰杂交,猫头鹰第二天生了一个硕大无朋的蛋,后来孵出了一只猫。
每次他捣鼓出一种新动物,都会赢得我们很多的赞誉,我们也都很恳切地把他当神一般的人物看待。
后来,这位“神”飘飘然了,他被胜利的喜悦冲昏了头脑,他做了最后一次大胆的实验。
那时候,猪在那个部落的图腾中也是被人当神来崇拜的。他自己跟头猪杂交了,那头猪怀上了他的种子,在那头猪十月怀胎的日子里,他细心照顾在它身边,他热切地希望这头猪能给他生个小“神仙”出来。
在一个有着如血夕阳的黄昏,这头猪生下了一个猪头人身的怪物,一出生就叫他“爸爸”,他被吓疯了,我们也被吓坏了。我们齐心协力捉住了那个怪物,掘了一深坑,把它活埋了。
它在那坑中凄惨的叫声、绝望的神色和溢出眼眶的眼泪在每个参与活埋的人心中如同刀子般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但
它
终归是被活埋了。
只是我们都不知道,后来有个叫吴承恩的同志把他写入了《西游记》。
失败与成功并存,人类的畜牧业就这样在磕磕碰碰中发展了起来。
七、火焰篇
那时候,并没有“野蛮”、“未开化”、“蒙昧”等字眼和概念,因为大家都一样,对生活也都习以为常。没有参照的对象,任何形容词都不存在。没有“大”,哪来“小”;没有“远”,哪有“近”?同样,没有“文明”,哪来“野蛮”?
我们茹毛饮血、生吞活剥。我们吃肉,常常都是吃出一嘴的鲜血,一嘴的毛,我们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催,直到有两件事改变了我们的观念。
那年夏天,我们中的很多人开始从粪便中拉出一米多长的虫子,那是非常可怕的虫子,通体乌黑,有着尖锐的牙齿,身上也布满了倒刺。随后,有些人就开始肚子痛,腹涨,肚子肿胀得跟孕妇似的。有人死了,死后从肚子中钻出无数的那样的虫子。
我们都吓坏了,都不明所以。有位一把胡子的智者根据他多年的生活经验,总结、排除、锤炼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让我们震惊。他说,是因为生肉中有大量的虫卵,人吃下去,就会孵化出大量的虫子。他把这种虫子以他的名义命名为“马老爹猪肉绦虫”,因为他叫马老爹。并且他号召人们以后不要吃肉。
马老爹的理论让我们非常愤怒,不吃肉,那点粮食如何能糊口啊?于是人们仍旧吃肉,仍旧有人死去。
那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天气出奇的闷热,太阳挂在当空,并不明亮,似乎有些按红的波浪漂浮在太阳表面。
天空乌蒙蒙的,象一块巨大的毛玻璃,人都好象在水中,影象都是模糊的。
我们站在田野里汗流浃背,没有人知道这奇怪的天气征兆着什么,连那位智者马老爹都不知道。
后来的一切就象做梦,从天空中猛地打了个雷,非常响,几乎把我们的耳朵都震聋了,接着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一个闪着蓝色光芒的火球坠落到不远处的树林里。
我们楞了半晌,不约而同地走向树林。我们都看到那个蓝球在地上滴溜溜地转动,把我们的眼睛都转花了。
我们谁也没料到,它转着转着突然爆炸了,巨大的气浪把我们每个人都掀了出去,随后树林中就燃起了熊熊烈火。
我们顾不得身上的疼痛和被灼去眉毛头发的难堪,都从尘埃里爬了起来。
每个人脸上都有种敬畏的神色。我们仰望那巨大的火舌舔噬着天空,把整个天空映成艳红的颜色;那滚滚的灰白的浓烟腾空而起,好象无数的骚动的巨龙张牙舞爪,向我们袒露它们狰狞的嘴脸。
这些前所未有的景象把我们镇住了,每个人的心脏都象只小喷泉似的“突突”跳个不停。
灼热的气浪把我们裸露在外面的体毛都燎得打卷了,浓烟也呛得我们涕泪俱下。但没有一个人敢动一动,甚至连呼吸都停止了。只有耳边不断从烈火中传来野兽的无比凄惨的叫声……
这场大伙持续了三天三夜,烧掉了老大一片树林子,烧死了无数的野兽和飞禽,甚至连我们辛辛苦苦建造起来的窝也在那场大火中化为乌有。
大自然是公平的,它在用天灾来教训我们的同时,也会把福音赐给我们。
比方,那场大雪让我们变得勤快起来,而这场大火,却又让我们认识到这种新事物妙不可言的好处。
开始没人胆敢踏进那片火灾区半步,因为马老爹声称,那是一块被神惩罚过的地方,是一块不祥之地,走近的人都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我们信服了一脸郑重的马老爹,因为他的胡子比我们的头发都长。
人类往往是好奇的,也只有这种好奇的探索精神才能打破故步自封的僵持局面,于是,人类才会进步。
在大火后的第三天,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我们中的一位有“吃第一只螃蟹”勇士精神的同志,跑到了火灾遗址,并吞食了第一块熟肉。
第二天,这位吃得满嘴流油、红光满面的“勇士”回来了,他开始大肆宣扬熟肉的美味。
他没有华丽的辞藻,他的词汇中并没有“谗涎欲滴”、“琼浆玉露”、“美味可口”、“齿颊留芳”、“脍炙人口”和“此味只应天上有”之类的词语,甚至连句“我差点把舌头都吃下去”的话也没有说。
事实胜于雄辩,他只是大张了嘴巴,让我们每个人看他满牙缝的残留的肉丝,并让我们每个人闻他口中的气味,在他恶劣的口臭中,我们都闻到了一股奇异的香气——烤肉的香气。
这种香气让我们如痴如醉,有几位女同志几乎克制不住要跟他亲嘴了。
毫无疑问,这种香味征服了我们,每个人都被勾得食指大动,蛔虫都在我们肠子里团团地跳舞。
所有人都疯狂了,我们粗暴地推开那位还试图阻止我们的马老爹,争先恐后地奔向那片被大火肆虐过的树林。只是谁也没有想到,马老爹过后竟也跟了过来,并且抢肉抢得比谁都凶狠,那张缺了好几颗牙齿的豁牙的嘴巴吞吃了比谁都多的熟肉。我们恨不得打他一顿。
后来就经常看到有许多人站在田野里“猴子看天”,我们都迫切地希望老天再赏赐个火球下来。
人们开了洋荤,再吃生肉难以下咽啊!
但老天并不是总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它的行为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于是,终归再没有火球落下来。
没办法了,想吃口熟肉只能靠自己了。
你们看,人类为了自己的“懒”和“馋”究竟能做出多大的牺牲。
起先,有位天才的同志经过潜心钻研。他发现木头跟石头是不同的。木头能够生长,象人类的肌体一样,于是,他就把它定义为“有肌体”,而石头是不能生长的,就是“无肌体”。只有“有肌体”能够燃烧,并且有一定的“燃点”,只有温度达到或超过它的“燃点”的时候,它才能燃烧。
更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位天才的同志竟然发现了“摩擦生热”这个大自然的秘密。
我们都没读过“希腊神话”,当然也不会象“伊阿佩托斯的儿子”“普罗米修斯”那样“用茴香秆从上帝的太阳车那里盗取火种”,不仅如此,就连最富有想象力的同志也不会为了一头“神牦牛”而从“格拉丹冬雪山上”象那群“勇敢的康巴汉子”那样“从太阳那里引来火种”。
我们都是平庸的,所以除了自己动手迎接光明外,别无他法。
天才同志系统归纳了他的研究成果,经过推理、加工、浓缩、升华,使之在实践上更具有切实可行性。
他创建了一套完整的名为“星火计划”的理论。他完成了他的个人使命。他可以休息了。剩下的就交给我们这些蠢人去做吧!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在这个时期就开始萌芽了。聪明人“骨碌、骨碌”眼珠工夫思考出来的点子,就够我们这些笨蛋忙活一辈子了。
“星火计划”从理论的建立到实际生产中的运用并没有经过太长的时间。
很快,第一簇火苗就战战兢兢地从某一位同志的石钻下的木头上冒了出来。
这简直是人类的一个盛大的节日,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伟大的时刻吧——三星正南!
火首先是运用的人类的饮食中,这无疑是明智的,后来人类的新技术大部分是首先应用到斗殴中。
人们真是越活越糊涂了。
天天吃熟食的人类的身体素质提高了,寿命也得到大幅度的延长,人们的生活水平做了一次巨大的飞跃。煮熟的蛋白质转化成一种神奇的力量,以迅不可挡之势贯通了人类禁锢万年的大脑——人类开窍了。
毫无疑问,火的出现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开端。
八、氏族篇
人类是圆滑的一个种群,象块面团一样在大自然的大手里变化出各种形状,他们顺应环境的变化,合乎“适者生存”的法则,于是人类才能如履薄冰似的继续发展下去,而没有象恐龙那样在鼎盛的时期灭绝。
人类真他*的是狡猾的一群,大大的狡猾。
我们的窝在那场大火中化为了灰烬,我们谁也没有勇气再造一个窝。我们得另觅一个牢靠、安全、防火的住处。
空气是不会着火的,但我们不能象鸟儿那样谁在空中;水里也是安全的,但我们不能象鱼儿那样住在水里。我们是无能的爬行动物,爬行动物有他们特定的栖息场所。
我们赶出了山洞里的牛鬼蛇神,并霸占了它们的住所。
这就是弱肉强食的残酷。
一大群本来象沙子一样不可兼容的个体,一下子塞到了同一个山洞中,而没个人都是愣头愣脑的,丝毫没有群居的观念。我们就象一群浑身是刺的豪猪,为了取暖挤在了一起,但距离近了,彼此都会被刺到,而如何能在保持距离的前提下取暖,这是最重要的。
顺理成章,我们需要制定一些行为规范,并需要一位德高望重者出来主持大局。
我们曾坚定地认为马老爹肯定能够脱颖而出,因为他是那么地有思想有见地。但后来,我们失望了。我们注定要被一群女人统治一段时期。
女人相对于男人在生存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她们曾让我们羡慕不已。
她们的性器是多么简洁流畅啊!只是简简单单的一道弧,再简简单单地覆上一层毛发,就构成了功能俱全的生殖器。
一点都不累赘,也不会暴露身份。
你看到那里只有一层毛发的人,你不要武断地辨别“她”的性别,也许是个阳具躲在毛发后的男人呢;而你看到有人底下挂着根风干的腊肠和两个皱结的核桃时,那肯定是无法遁迹的男人。
当我们追逐猎物而被性器的摇摆延缓了速度时;当我们翻越栅栏而被狠磕了一下蛋蛋时;当我们撒尿的家伙被蚊虫叮咬而痒不能挠时;当我们好好地走着路而突然被狗熊掏了一下裆时。
你能不嫉恨胯下那一嘟噜肉?你是不是在梦中曾用一把镰刀象收割高粱一样把它连根割去,或用锤子象敲核桃一样把它彻底锤爆?
这都是正常的,它并不能给你带来自豪感和优越感。
它是个懦夫,当受冷或恐惧时,最先收缩的肯定是它。
而女人的阴道却是大路的延伸。
我们无比羡慕女人,我们都有“乳房崇拜”。
在那个时期,女人的变化是巨大的。
她们好象是在一夜之间完成了“超前进化”,她们象脱毛衣一样褪去了一身毛发,变得跟刚剥了壳的熟鸡蛋一样光滑娇嫩。她们让我们这些毛豆侯的没进化好的男人惊奇赞叹。
她们自己也变得趾高气扬起来,变得矜持起来。她们时刻都要表现得跟我们这些臭男人不同,她们站在我们中间好象鹤立鸡群,她们走平地都能踩出蹬梯子的味道,她们常常顾影自怜,她们在一切反光物体前观看自己的容貌,哪怕是一泡尿,也能让她们臭美好久。
更可怕的是她们在我们火热的目光下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是个宝了。
她们以前毛茸茸的身子我们是正眼不瞧的,而当我们怀着满心的喜悦去欣赏她们变化后的身体时,她们却不给我们看了。
她们把兽皮或采来的树叶花朵,用线串起来,围在腰间,把她们简洁的生殖器包裹得严严实实,甚至她们的胸前的那两个婴儿的干粮袋也金贵起来,我们再也看不到了。
我们愤怒了,我们觉得自己吃亏了。我们也用物品遮挡住自己的东西,也不让她们看到。
人类是愚蠢的动物,在男女互相的隐藏中,我们丧失多少可以大饱眼福的机会?
以后的春天象是颠倒了黑白,女人不再去勾引男人,哪怕是春潮泛滥,她们也能以大无畏的克制力不让自己做出失态的行为。
她们拿起架子来了,她们象磐石一样岿然不动。
我们感到责任重大,我们无法自己完成传宗接代的重任。我们必须去取悦她们,虽然这让我们感到耻辱。
以后就常常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女人洗把得新鲜水灵,高高地端坐在麦秸垛上,让春天的阳光沐浴得跟个菩萨似的。一群男人乔装打扮。有的在脖子上挂一串兽骨,有的在胸前粘上假胸毛,有的把脸涂抹得五颜六色,有的甚至在屁股后绑个开屏的孔雀尾巴。然后在那个女人面前跳一些自编的舞蹈,吼一些自己才能懂的情歌,并把地上的麦秸抛洒得到处都是。
那个女人从参加“选美”的男人中间,挑选出穿得最有个性,吼得最具深情,跳得最有韵律的男人,然后把他带到一处阴暗的角落,把他强奸。
男人成了女人的奴隶,每个女人都幻想自己是女王,挥舞着带着倒刺的皮鞭,把男人放倒,怒气冲冲地喊着:跪下,你这只可怜的虫子,我是你的主人,伸出你那卑贱的舌头,象狗一样美美地品尝我那高贵的*吧!
啪啪!
女人并没有多少致命武器,她用生殖这条锁链把男人当狗一样地拴了起来。
然而,女王只有一个,如何从那群普遍凌驾在男人头上的女人中选出女王,这并没有费太多的周折。
女王诞生了,她叫生姐。
为何是生姐而不是别人?因为她能生呗!
生姐是那种让男人一看就想把种子播给她的女人。
她有一头群蛇一样瀑布似的的头发。
她的额头象块大红薯片。
她的眼睛跟妖精似的闪着妖异的光芒。
她的鼻子很挺拔,很倔强,跟熊的苦胆似的。
她的嘴唇十分厚实,饱满得跟豆荚一样,她总是不停地用粉红色的舌头舔它。
她的上唇有纤细的汗毛,经常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子般的光泽。
她的乳房是浑圆上翘的,有西瓜那么大,她的乳头是黑红的颜色,跟两粒大个的红枣儿似的。
她的胳膊象两段鲜藕,她的腿象两跟胡萝卜。
她身上的一切都象是吃的,在那“饥者歌其食”的日子里,她能让每个男人的眼睛变绿,流出馋涎。
她浑身散发着野性的魅力,她的身体好象在时刻暗示我们:来吧,来干我吧!
许多男人在她那里辛勤耕耘,并播下种子,她以每年一个的高效率生着孩子,持续了十年,且保持势头不减。
她让每个女人自卑,而每个女人让我们自卑。
于是,她做了族长。
生姐是有魄力和眼光的,她“任人惟贤”,主张“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她给我们分派任务:善于打猎的就去打猎,精于种田的就去种田,会放牧的就去放牧,会编制的就去织鱼网、做衣服。
她并没有把自己当“官”来看待,她跟我们一起栉风沐雨,干的活儿不比我们少。
收获的粮食和猎物都上缴上去,储存起来,由她统一分配,有了储粮,以后在遇到天灾的时候,也不至于挨饿了。
她把我们这一大群管制得服服帖帖,把这个氏族治理得井然有序,她成了我们的脊梁和主心骨。
母系氏族社会是人类群居后的一种社会形态,这时出现了分工协作,生产力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平均分配”也从这时开始。
社会是张网,它用看不到的蛛丝把人牢牢地凝聚了起来,毫无疑问,母系氏族的出现是人类从“无序”走向“有序”的开端。
画外音
长期的生活经验,使人们认识到近亲 婚配的缺陷和外婚制的优越,这时,氏族公社开始萌芽,到旧石器时代的晚期,也就是新人(晚期智人)阶段,氏族公社正式形成。氏族内不得通婚是氏族公社的根本规则。直系父母兄弟姐妹之间的婚配是被排斥的。一氏族的一群兄弟只能与另一氏族的一群姊妹交互群 婚。在这种婚姻形式下,一女子与很多男子发生关系,生的孩子只能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血统也只能按母系计算。同一始祖母生下的后代组成一个氏族。这种以女性为中心的氏族社会,便是母 系氏族社会。
在氏族社会的自然分工中,男子从事 狩猎活动,女子则从事采集活动。经 验的累积,使妇女们认识到许多植物生长的规 律,从而促使了农业产生和发展。而妇女就成了 初期农业的承担者与领导者。在母系氏族社会中,妇女承担的农业 劳动,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稳定的产品,改善了物质生活。相反,男子从事狩猎活动,常常不能保证有足够的收获,因而在氏族中的地位不如女子。妇女还发明了编织工艺和制陶技术。另外,妇女还要承担抚育子女、教育培养后代等重要任务,她们的工作是维系氏族生活的根本保 证。
母系氏族是以母系血统为纽带而组成 的一个社会生产、生活单位。在这个社会里,生产资源公有,人们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氏族成员死后随葬少量物品,氏族财产由氏族集体继承,氏族男性成员无继承权。这种共产制家庭经济,是母系氏族社会中妇女统治的物质基础。
母系氏族社会以年长妇女为氏族长,全体氏 族成员有权选举或罢免氏族长,氏族首领负责领导生产和管理生活、对外联络,但无特权,遇有重大事件,要召开氏族议事会集体讨论决定。
以上是科学的母系氏族研究。我们只是戏说,与历史不符的地方,以科学为准。
九、文化篇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们不认识上帝,也无须逗他乐。但我们却始终在做给上帝呵痒这样的工作。
人类总是迷惘的,人类总在不断找寻答案,当一个迷惘被解释后,就有会有新的更多的迷惘出现,当人类把新的迷惘解决掉后,人类又会发现,先前的迷惘的解释根本是错误的。
人类总在解释迷惘,总是被迷惘所迷惑。
人类最先叩问的是自身。人类总想问问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什么,活着是什么,是为了什么。
这时,有位同志突然从火堆边跳起来,对周围那些蒙昧的同志说:操他*的,我们原来是群猴子,我们活着是为了吃饭。
我们惊愕了,张大了嘴巴,每个人的扁桃体都在火光下若隐若现.还没有人曾给我们下过如此精辟的定义,也没有人对我们活着的目的进行过如此深刻的思考.
于是,我们为他报以热烈的掌声.上帝听到了,也会忍不住会为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喝上一声采的。
原本围坐在火堆边懒洋洋的,五官四肢,连同脑筋一概停止运动的我们活跃起来。
这时,另一位更有文学色彩的同志站起来,用文学化的语言描述了我们来自何方,他说:我有个花骨朵,我把我的花骨朵放到她的花盆里,后来,开花结果,有了小孩,我想我们也是这么来的。
另一位同志也触类旁通,他讲述得就更接近问题的本质了,他说:我有一只鸟儿,我把我的鸟儿放到她的鸟窝里,后来鸟儿下了一个蛋,蛋孵化出小孩。
气氛热烈起来,每个人都参与了讨论,我们讲得唾沫横飞,我们抚摩着自己的“鸟儿”,想着生姐水淋淋的鸟窝,有几位同志忍耐不住,到女人的“鸟窝”那里“下蛋”去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这群思想家就对我们共同的疑惑展开了无休无止的辨析,有些问题豁然开朗,但更多的问题越描越黑。
老仓越来越奇怪了,当我们聚集在一起快乐地意淫的时候,他却一个人跑别的地方去,或是盯着太阳一眼不眨,或是看着月亮不眨一眼,或是去看那些山啊水啊牛啊羊啊的,甚至一棵狗尾巴草他都能研究上好久。后来就经常看到他一个人闷不做声地用石头在地上画一些奇怪的符号。
我们都认为他傻掉了,果然。
有一天,老仓一脸诡异地跑来,神神秘秘地对我们宣布:他在造字呢。
我们对他示以翻着的白眼,并嗤之以鼻。
我们没有文字,还不是这样过来了。
字?
去他*的。
有什么用?
老仓锲而不舍地研究了下去,我们终究没有想到他的研究有一天会派上用场。
羊在人的眼中都是一个模样的,羊群中少了一只两只的,人根本不会发觉。我们放的羊开始越来越少,其实,那大牲口都在暗处藏着呢,趁我们不注意,就叼一只去。开始是老大的一群羊,放到最后就剩余一两只了。我们没有数量观念,只是莫名其妙地觉得这不应该。生姐常为此大发雷霆。
老仓的数字研究初有成果。他发明了“偶数”和“奇数”,并把这教授给了我们。
以后我们放羊时,口中就念念有辞:一对,一对,一对……单?明明那会儿数着没有单出来的,怎么这会儿多出一只单个的羊?肯定被大牲口叼去了。然后,一路狂追,追上了就捻弓搭箭,就那样把那羊从大牲口嘴里救回来了。运气好的,还能把大牲口猎杀。
当然,这种方法有它的缺陷:大牲口一次叼两只羊,我们就束手无策了。
但等到老仓彻底地完成他的数字研究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我们都相信他能数清天上的星星,他自己也承认了。
于是,我们就再没放丢过一只羊。
老仓的文字研究也取得了令我们瞩目的成就,他在一张羊皮上用木炭写了一篇文章。
那真是一篇天书啊!那一个个象小树枝插起来的有胡桃那么大的字在羊皮上冷笑,我们都看得头晕目眩,大气不敢出一口。
老仓小心翼翼地捧着那张羊皮,象宣读圣旨一样抑扬顿挫地念道:山是山来,水是水;牛是牛来,羊是羊。
老仓的文字研究在后来也象一切学术研究一样,无可避免地堕入了下流。
他把女人性器研究了很长时间,按他的话来说就是:把女人性器掰开了揉碎了由内到外由表及里由动态到静态都做了细致的观察和科学的研究。
他创造出一个新字,那个字长得象只牛眼:两个半圆弧夹着一个黑洞。老仓把它念作“日”(bi),并且一脸猥亵地说:这象不象个活塞,象不象那种令人愉快的事儿?这个“日”可以一字两用的。
我们又一次惊愕了,每个人都陷入深深地思考中去,好象那个字有种神奇的魔力吸引了我们。
空气一下子沉闷起来。后来,有个脑筋转得特别快的同志恍然大悟地说:“日”(ri)他的妈的“日”(bi)啊。
所有人都恍然大悟了,一起说道:“日”(ri)他的妈的“日”(bi)啊,原来如此。
每个人都乐呵呵的,一脸轻松。
老仓更是合不拢嘴。
人类总有寻根究源的劣根性,他们表面上显得数典不忘祖,而骨子里还不是“人类历史渊源流长”的虚荣作祟?没有人希望自己的祖先是只丑陋的猴子,我们得自己制造自己的祖先。
那是一个太阳明晃晃的正午,生姐把我们招集在一起,说是召开氏族大会。
我们拥挤在太阳下,流着汗,窃窃私语。
生姐裸露着上身,硕大的古铜颜色的乳房被太阳晒得油汪汪的,折射出神圣的光彩。
她是女神,是的。
生姐嘹亮的如银子般的天籁之音流淌出来,会场寂静了。
生姐宣布她找到了我们共同的祖先。
生姐拍拍手,老仓应声而现,他搬着一块巨大的青石步履维艰地走到会场中央,他异常小心地费力地放下那块青石。
我们迷惑了,那块青石光滑的一面杂乱无序地划着无数的线条。
我们凝视那些线条,我们惊讶了,那些线条在每个人的视网膜上都有机地结合成一个人身蛇尾的怪物。
她有一双硕大无朋的乳房,她的腰肢纤纤,自腰以下就是生着鳞片的蛇的尾巴。
她是氤氲的,她的面孔依稀象是生姐的面孔。
我们着魔了,谁也没有发觉马老爹悄然登上会场。马老爹的声音有种催眠的魔力,他用沙哑低沉的嗓音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
在很久很久以前,这个世界上没有你也没有我,只有一位名叫女娲的神灵,她人身蛇尾,她有通天彻地的神力。
她是寂寞的,她身长在水边顾影自怜,她便用泥巴按照自己的模样捏了许多小人,她朝那些泥塑木偶吹了一口气。他们全活了,簇拥在她身边喊她“妈妈”,她累了,她从山涧扯来一根千年藤条,蘸取泥水,凭空一甩,泥点落在地上,变成数不清的人。有男人也有女人,他们又自我繁殖,于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世界热闹起来,女娲满足了,她欣慰地睡去了。
未完待续
古月草于湖南师大学生宿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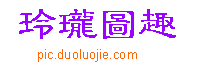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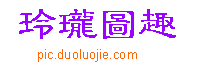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王吧已死
王吧已死
 Post By:2004/4/16 12:24:00
Post By:2004/4/16 12:24:00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王吧已死
王吧已死
 Post By:2004/4/16 13:50:00
Post By:2004/4/16 13:50:00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名人堂成员
名人堂成员
 Post By:2004/4/16 15:22:00
Post By:2004/4/16 15:22:00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名人堂成员
名人堂成员
 Post By:2004/4/17 23:49:00
Post By:2004/4/17 23:49:00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论坛元老
论坛元老
 Post By:2004/4/18 0:07:00
Post By:2004/4/18 0:07:00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我丢了一只猫
我丢了一只猫
 Post By:2004/4/18 12:09:00
Post By:2004/4/18 12:09:00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名人堂成员
名人堂成员
 Post By:2004/4/19 12:39:00
Post By:2004/4/19 12:39:00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论坛元老
论坛元老
 Post By:2004/4/19 16:30:00
Post By:2004/4/19 16:3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