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eggy
前一篇提到海明威常去,位於聖米歇廣場上,一家雅淨的咖啡館
那麼,花神咖啡館,或許就是我心靈的一片靜土
在巴黎,之於我,像是半個家的地方
歷史盛名,使得花神咖啡館成了觀光客充斥,時而吵雜不堪之地
也嚇走不少慕名而來的遊客
我也承認,其中有些侍者的確高挺著三十度角鼻尖,令人生畏...
話雖如此,當我試著對花神咖啡館放開自己的保護層,才逐漸體會:
Rendez-Vous au Café de Flore ... - 相約花神咖啡館 ...
這句Logo的真正含意....
也許,可以讀讀這一篇:巴黎咖啡館的味道
周四晚上的花神咖啡館是人氣鼎盛的,氳煙繚繞的四周讓我有些喘不過氣來。因此我三番兩次爬上樓,緩緩走入二樓洗手間。那是個可以稍微逃離這個可怕世界,讓被煙霧和噪音轟炸的頭腦有恢復思考能力機會的小靜地。洗手間令我驚訝,地板上的碎瓷磚,陳舊而復古,角落擺放著一台似乎可以用手搖撥接的公共電話。我感覺,不是刻意放置的,倒像這一百年來他們都不曾換過裝潢。這不是不可能。
洗手間和通往一樓木製樓梯之間有個櫥櫃,林林總總的東西讓我嘆為觀止。一方面覺得有點可笑,另一方面我卻思考,如果將來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小小房間裡,拾起印著翠綠色「Cafe de Flore」的白瓷杯,為自己沖泡一壺熱騰騰花茶、咖啡,什麼都好,說不定真能讓自己回到在巴黎的心情?那麼,不算便宜的白瓷杯也就值得它的價錢。除了大杯盛卡布其諾咖啡、中杯盛茶、小杯盛濃縮咖啡等不同容量的白瓷杯組和白瓷壺,盛裝熱巧克力的銀壺也在櫥櫃裡陳列著。要不,還有印有花神咖啡館地址的盤子、菸灰缸、銀匙、筆記本、水瓶,封面有花神咖啡館照片的書、攝影集。也許太多人喜歡這裡的方糖,如果我沒記錯,印有花神咖啡館的方糖也是可以買的。當然,那本米白色襯著鉛筆素描的菜單,一句「我們在花神咖啡館見面吧……」,價值是三十六法郎。如果喜歡的話,托盤、侍者的圍裙也能買。
竊笑花神咖啡館的同時,心裡突然有一股遺憾,想想自己不過是個被商人瞄準的目標,而巴黎有名的咖啡館如今也因為名氣開始做些沒氣質的事了。雖然這麼想,我的心裡卻在盤算,荷包裡的錢,足夠帶幾個杯子回去?一直想帶回波士頓給好友華的禮物有著落了,這個杯子或者能讓她重溫在聖傑曼德佩區蜜月的滋味,我不好意思在櫥窗前站太久,所以隔一小段時間,就走上二樓,偷偷摸摸在洗手間照幾張相,然後順便在櫥窗前逗留,糟糕的是,每經過一次,發現自己想帶回去的東西就多一樣。
走回暫時屬於我的木桌,再一次和那位體面的中年男人擦身而過,「你們有明信片嗎?」我問。巴黎有特色的餐廳一角經常放置著自製的明信片,精緻特別而且免費,雖然他們從不主動拿給客人。我總是藉故在餐廳內走動,觀察有紀念價值的明信片藏在哪個不起眼的角落。
「當然有,跟我來。」他很有魅力地一笑,帶我走到花神咖啡館敞開的門口。一片軟木板上貼有二十張之多不同的明信片——黑白、彩色、日景、夜景、咖啡館內談笑的人們、咖啡館關門後疊放整齊的籐椅、咖啡館外街上急行的男女、水彩畫、素描,每張都一一編好號碼——一張六法郎,想要幾張都行。
「妳要哪幾號告訴我?」心裡一邊咕噥,一邊衡量如何在二十多張明信片中取捨,老實說,明信片的質感相當好。我看上三張黑白照片。
「一起算在帳單裡吧。」我說。
「對不起,我們沒有免費的明信片。這個送妳好了。」他遞給我一張米黃色,印著「我們在花神咖啡館見面吧……」和翠綠色「Café de Flore」字樣的卡片,卡片中央是一張泛黃的照片——從聖傑曼大道街角看過來的花神咖啡館。
「妳等等,我去後面找妳要的卡片。」
他再度出現在我桌前,遞上明信片的同時,也附上一張名片。
「吃過了嗎?要不要叫點什麼吃的?」他問。
「沒關係,我不餓。」
這句話是違背良心的,來到聖傑曼德佩區前我曾在經過的中國快餐店買了比桌上這壺茶還便宜的炒麵,因為進來得早,還沒機會吃。眼看對面牆上的時鐘一個小時一個小時轉過,空腹喝完一整壺茶的我早就餓得有點頭暈。剛才隔壁男女的鴨肉沙拉上桌的時候,我仔細地研究了其中的每一道佐料,再試著把它們畫在本子上。
「妳工作得太認真了。」法蘭克斯說。看過名片之後,我確定他是這裡的經理之一。
我繼續埋首,茶杯已空。雖然餓得難過,我還是決定不再叫任何東西,一份「花神(Le Flore)」餐,可以換幾個印有「Café de Flore」字樣的杯子也說不一定。
從走進花神咖啡館第一步,我就有一種奇怪的矛盾感。吵鬧、菸味、頭痛、數不清的觀光客、窄小的座位、陳舊的擺設,我一方面努力地收集在這個地方「合法」可以留下的紀念品:杯墊、茶壺把手上的隔熱紙、方糖的包裝紙、老闆的名片、餐巾紙,一邊取笑自己來巴黎數次,又待了一段不算短的時間,卻還在做觀光客巴黎三日遊的功課之一。總之,到此刻為止,除了那只銀壺、白瓷印著翠綠色字的茶杯,洗手間外那台古舊的電話機,花神咖啡館沒有任何令我高興的地方。
一位侍者把桌上所有茶具和因為撕壞所以被留在桌上的方糖紙、沾到茶所以沒被「收留」的餐巾收拾乾淨。剛才法蘭克斯問我「想喝杯香檳嗎?或是紅酒?」時,我笑著搖搖頭。所以雖然一坐好幾小時,其實只點了一壺三?三法郎的茶。我想這個動作應是侍者委婉的暗示?這畢竟是做生意的地方。把桌上散亂的雜記紙筆簡單整理,我餓極了,該是回家的時候,背袋裡的炒麵正在呼喚我。
幾乎收拾好準備離開的時候,那位約有六?多歲的侍者再度從廚房出現,手中高高地端著銀製的托盤,白瓷茶具完美地擺放在托盤上。這幾個小時內,我開始發現這是一種迷人的動作。他沒有走遠,停在我那距廚房門口只有一步之遙的方桌前,彎下腰,很有禮貌地放下托盤。托盤裡是滿滿一整壺桔茶,另外,小盅開水和牛奶也是滿的。換上的白瓷茶杯碟上已經找不到因為我大意而溢出的茶漬,茶壺的把手上加上新的隔熱紙墊,兩顆方糖、包著印有花神咖啡館字樣的紙,整齊地放置在白瓷碟子上。我看了看那位侍者,他對我點點頭,微鞠著躬,然後快步離開繼續招呼其他桌客人。
一壺茶大約有四杯半的容量,喝下四大杯茶後,我想自己肚子裡大概全是水了。奇怪的是,九點半,咖啡館裡嘈雜的遊客漸漸散去,一下子安靜下來,不再那麼煩躁可憎。新沏好桔茶出現在我面前時,一股幸福的感覺湧上,電影膠卷快速轉動著,花神咖啡館裡的空氣突然溫柔起來。我重新拿出收好的筆記,決定再待一會兒,即使我一點也不想再喝茶,而且飢餓已讓我暈眩,幾乎無法思考。但,我想自己必須給一壺新沏好的茶一點面子。
進入花神咖啡館時天空是微陰的。人少之後,我才意識到街上淅瀝的雨聲。除去可怕多國語言混雜組合而成的噪音,將近?點的咖啡館突然像變了一個地方似的。
觀光客消失了。隔我兩桌的中年男人桌上散置有?來本雜誌,他蹺著腳,漫不經心地翻著,一邊拿起面前的濃縮咖啡。男人左手邊坐著一位高瘦的老先生,拿著放大鏡仔細地讀報紙。老先生面前有一盤剛出爐義大利麵之類的東西,熱呼呼的白煙從麵條之間撒得均勻的乳酪屑中冒出,老先生一邊嚼著麵一邊讀報紙,他每吃一口,隔著三桌的我都能感覺到來自自己胃羨慕地抗議。我再一次把面前的茶杯盛滿。
一位戴著暗褐色鴨舌帽的老先生拄著柺杖緩慢地側身繞過其他桌椅,再側身坐進我隔壁的座位。他穿著深灰色西裝,脖子上深紅色領帶繫得?分漂亮。老先生小心地把柺杖靠在暗紅色皮沙發的邊緣,這個位子不大,他凸出的肚子正好挺在桌緣。我們距離得?分近,因此我可以仔細地觀察他。老先生或許有七?歲了,稀疏的銀灰色頭髮很整齊地往後梳,我注意到他柺杖上方有著非常細膩的雕刻。深灰色西裝之下令我吃驚的是一雙深咖啡色看來質感相當好的休閒鞋。老先生從有點壓扁了的皮公事包中拿出四、五本書丟在桌上,然後就一頭埋入書本的世界。我不記得他點了咖啡還是茶,甚至覺得他可能什麼也沒點,只記得他沉浸在書中緩慢而出神的表情。
法蘭克斯坐在靠門口的位子用餐,剛才他走過來的時候,遞給我兩片巧克力。
「好餓,我一直忙到現在,終於可以吃飯了。」他說。
「可以幫我照張相嗎?」我說。
「當然好,和我一起嗎?」
我難得在幾家咖啡館餐廳想為自己留下紀念照,但每回最後的照片上都會多出一些侍者或廚師。我笑著點點頭,法蘭克斯馬上喚來一位年輕侍者。
「等我吃完飯請妳喝咖啡吧。我們聊聊?」
我的肚子裡裝得滿滿的茶,目前百分之一千不想喝咖啡。尤其聽到
「等我吃完飯」這幾個字之後。不過,一天下來,我沒有和任何人交談,彷彿自閉症似地對著本子寫了一個晚上,讓嘴巴運動一下也不錯。法蘭克斯身邊坐著一對五十歲上下的男女,男人半傾著上身往女人的臉龐靠近,那是一種求愛的表情和姿勢。而男人身邊的女人打扮成熟嫵媚,卻流露出一臉小女生嬌羞的表情。她低著頭,任由男人撫摸她的手指。我突然想到,如果爸爸目睹這一幕,一定會說:「那八成是情婦。」他來巴黎的時候,我們常常一起討論餐館裡其他客人之間可能的關係。
我小心撕開法蘭克斯遞上巧克力外層的白色包裝(然後把印著花神咖啡館圖案的包裝紙夾進我的記事本),這兩顆巧克力此刻對我而言彷如救命的仙丹,上次進食是下午三點。我迫不及待想吞下任何食物。
掀開金色錫箔紙時我卻怔住了。
那是一顆讓人沒有辦法一口「啊」地就吞下的巧克力。雖然我做了前面一半的動作,那個「啊」卻在到嘴巴前停止住。巧克力上細膩的線條,是每一個經過聖傑曼大道轉角的人對花神咖啡館的第一個印象。大約二公分長三公分寬的深咖啡色巧克力上,像是用裝滿巧克力墨汁的鋼筆,細細地描繪出咖啡館給人的第一印象。我在筆記本上試著把這迷人線條描繪一次,畫完之後,才忍痛吃掉其中一顆,把剩下那顆收進百寶袋。
「來杯熱巧克力吧。」我說。肚裡有八杯茶,除了熱巧克力,我想不出還有任何一種液體在此刻能裝進胃裡的。威士忌,以後再說吧。
「我們的熱巧克力很不錯,妳真會點。」
「真的很棒。」法蘭克斯對我眨個眼,又加上一句讚美。
招呼侍者來的時候,四位年輕日本男孩說說笑笑地走進花神咖啡館。他們的頭髮是金黃色的,就像在電視雜誌上看到的日本年輕人。法蘭克斯和我使個眼色「等我一下」,快速地走到他們桌前。四個人站起來,一一和法蘭克斯握手,並擁抱著親吻臉頰。
「他們是隔壁幾條街一家日本料理店的服務生,每天下班之後,都要來這裡喝一杯。」法蘭克斯帶著笑容回來,一路上又以眼神和手勢和另外幾桌客人致意。這使我懷疑,自己是不是此刻店裡唯一不是熟客的奇怪客人。(喝一杯茶從下午坐到深夜,難怪老闆要來調查一下。)
沒有多久,三位穿著時髦高 性感的女性出現,頂著漂亮的髮型,長筒皮靴,低胸毛衣,很引人注意。她們也許剛從哪用完晚餐,看來心情很好,邊走邊高聲地說話,其中一位有濃厚的英國腔。看到法蘭克斯,三個人又輪流熱烈地和他親吻招呼,並用英文和法蘭克斯及其他侍者問好。
這是怎麼一回事,難道她們不是觀光客嗎?一位年輕侍者走向她們,給每一位女士一個吻,似乎雙方都很高興。現在看來,我是唯一進入咖啡館內沒有和法蘭克斯親吻招呼的人。
奇怪的是,昨夜,我獨自一人坐在丁香園靠近演奏鋼琴旁的一個位子。入夜時分,穿著淺藍色短袖襯衫看來?分隨意的一位老年男士從杯盤狼藉的座位走出坐上鋼琴椅。他彈奏著鋼琴邊低聲吟唱。當他離開鋼琴座走入酒吧區時,我驚奇地發現他似乎和大部分此刻吧裡的客人互相認識,至少,會互相親吻。那是一個在丁香園門外看不到的世界。雖然,海明威描述的丁香園正是如此,但,那不是超過半世紀以前的事嗎?
下一次走進花神咖啡館的時候,我也會和法蘭克斯親吻吧。說不定,那位六十多歲的侍者也會把臉龐湊上
文章是转的
顺便也介绍下这个咖啡馆(要是能去一趟那里 ……别做白日梦了……)
花神咖啡馆 Cafe de Flore
与双叟咖啡馆隔邻的花神咖啡馆,是于1865年开始营业,並自20世纪初便与现代文学难分难捨,30年代後期,花神咖啡馆一度成为法国文化
人碰头及交换政见与消息的地方,亦是毕卡索与夏卡尔这2位流放艺术家经常出现交流心得之处,所以花神咖啡馆在40-50年代,成为法国的知识份子、学者、作家的重镇,当代的文学理论和哲学思想,幾乎都是从咖啡杯裡探讨出来的。
营业时间: 07:00-01:00,全年无休
地铁站 : Saint-Germain-des-Pr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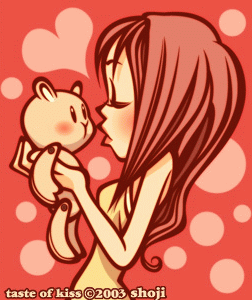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6/7/15 20:01:00
Post By:2006/7/15 20:0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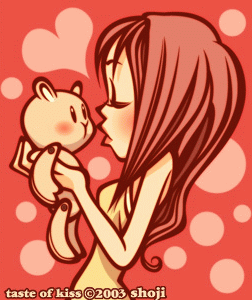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6/7/15 20:10:00
Post By:2006/7/15 20: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