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西,我回来了,几个月前一袭黑衣离去,而今穿着彩衣回来,你看了欢喜吗?
向你告别的时候,阳光正烈,寂寂的墓园里,只有蝉鸣的声音。
我坐在地上,在你永眠的身边,双手环住我们的十字架。
我的手指,一遍又一遍轻轻划过你的名字——荷西、马利安、葛罗。
我一次又一次的爱抚着你,就似每一次轻轻摸着你的头发一般的依恋和温柔。
我在心里对你说——荷西,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这一句让你等了十三年的话,让我用残生的岁月悄悄的只讲给你一个人听吧!
我亲吻着你的名字,一次,一次,又一次,虽然口中一直叫着∶「荷西安息!荷西安息!」可是我的双臂,不肯放下你。
我又对你说∶「荷西,你乖乖的睡,我去一趟台湾就回来陪你,不要悲伤,你只是睡了!」
结婚以前,在塞哥维亚的雪地里,已经换过的心,你带去的那颗是我的,我身上的,是你。
埋下去的,是你,也是我。走了的,是我们。
我拿出缝好的小白布口袋来,黑悠悠里,系进了一握你坟上的黄土。跟我走吧,我爱的人!跟着我是否才叫真正安息呢?
我替你再度整理了一下满瓶的鲜花,血也似的深红的玖瑰。留给你,过几日也是枯残,而我要回台湾去了,荷西,这是怎麽回事,一瞬间花落人亡;荷西,为什麽不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一切只是一场恶梦。
离去的时刻到了,我几度想放开你,又几次紧紧抱住你的名字不能放手。黄土下的你寂寞,而我,也是孤零零的我,为什麽不能也躺在你的身边。
父母在山下巴巴的等待着我。荷西,我现在不能做什麽,只有你晓得,你妻子的心,是埋在什麽地方。
苍天,你不说话,对我,天地间最大的奥秘是荷西,而你,不说什麽收了回去,让我泪眼仰望晴空。
我最后一次亲吻了你,荷西,给我勇气,放掉你大步走开吧!
我背着你狂奔而去,跑了一大段路,忍不住停下来回首,我再度向你跑回去,扑倒在你的身上痛哭。
我爱的人,不忍留下你一个人在黑暗里,在那个地方,又到哪儿去握住我的手安睡?
我爬在地上哭着开始挖土,让我再将十指挖出鲜血,将你挖出来,再抱你一次,抱到我们一起烂成白骨吧!
那时候,我被哭泣着上来的父母拉走了。我不敢挣扎,只是全身发抖,泪如血涌。最后回首的那一眼,阳光下的十字架亮着新漆。你,没有一句告别的话留给我。
那个十字架,是你背,也是我背,不到再相见的日子,我知道,我们不会肯放下。
~~
荷西,我永生的丈夫,我守着自己的诺言千山万水的回来了,不要为我悲伤,你看我,不是穿着你生前最爱看的那件锦绣彩衣来见你了吗?
下机后去镇上买鲜花,店里的人惊见是远去台湾又回来的我,握住我的双手说不出一句话来,我们相视微笑,眼里都浮上了泪。
我抱着满杯的鲜花走过小城的石板路,街上的车子停了,里面不识的人,只是淡淡的说∶「上车来吧!送你去看荷西。」
下了车,我对人点头道谢,看见了去年你停灵的小屋,心便狂跳起来。在那个房间里,四支白烛,我握住你冰凉苍白的双手,静静度过了我们最后的一夜,今生今世最后一个相聚相依的夜晚。
我鼓起勇气走上了那条通向墓园的煤渣路,一步一步的经过排排安睡了的人。我上石阶,又上石阶,向左转,远远看见了你躺着的那片地,我的步子零乱,我的呼吸急促,我忍不住向你狂奔而去。荷西,我回来了——我奔散了手中的花束,
我只是疯了似的向你跑去。
冲到你的墓前,惊见墓木已拱,十字架旧得有若朽木,你的名字,也淡得看不出是谁了。
我丢了花,扑上去亲吻你,万箭穿心的痛穿透了身体。是我远走了,你的坟地才如此荒芜,荷西,我对不起你——
不能,我不是坐下来哭你的,先给你插好了花,注满清水在瓶子里,然后我要下山去给你买油漆。
来,让我再抱你一次,就算你已成白骨,仍是梦里相思又相思的亲人呵!
我走路奔着下小城,进了五金店就要淡棕色的亮光漆和小刷子,还去文具店买了黑色的粗芯签字笔。
路上有我相熟的朋友,我跟他们匆匆拥抱了一下,心神溃散,无法说什麽别后的情形。
银行的行长好心要伴我再上墓园,我谢了他,只肯他的大车送到门口。
这段时光只是我们的,谁也不能在一旁,荷西,不要急,今天,明天,后天,便是在你的身畔坐到天黑,坐到我也一同睡去。
我再度走进墓园,那边传来了丁字镐的声音,那个守墓地的在挖什麽人的坟?
我一步一步走进去,马诺罗看见是我,惊唤了一声,放下工具向我跑来。
「马诺罗,我回来了!」我向他伸出手去,他双手接住我,只是又用袖子去擦汗。
「天热呢!」他木讷的说。
「是,春天已经尽了。」我说。
这时,我看见一个坟已被挖开,另外一个工人在用铁条橇开棺材,远远的角落里,站着一个黑衣的女人。
「你们在拣骨?」我问。马诺罗点点头,向那边的女人望了一眼。
我慢慢的向她走去,她也迎了上来。
「五年了?」我轻轻问她,她也轻轻的点点头。
「要装去哪里?」
「马德里。」
那边一阵木头迸裂的声音,传来了喊声∶「太太,过来看一下签字,我们才好装小箱!」
那个中年妇人的脸上一阵抽动。
我紧握了她一下双手,她却不能举步。
「不看行不行?只签字。」我忍不住代她喊了回去。
「不行的,不看怎麽交代,怎麽向市政府去交签字——」那边又喊了过来。
「我代你去看?」我抱住她,在她颊上亲了一下。她点点头,手绢唔上了眼睛。
我走向已经打开的棺木,那个躺着的人,看上去不是白骨,连衣服都灰灰的附在身上。
马诺罗和另外一个掘坟人将那人的大腿一拉,身上的东西灰尘似的飞散了,一天一地的飞灰,白骨,这才露了出来。
我仍是骇了一跳,不觉转过头去。
「看到了?」那边问着。
「我代看了,等会儿这位太太签字。」
阳光太烈,我奔过去将那不断抽动着双肩的孤单女人扶到大树下去靠着。
我被看见的情景骇得麻了过去,只是一直发冷发抖。
「一个人来的?」我问她,她点头。
我抓住她的手∶「待会儿,装好了小箱,你回旅馆去睡一下。」
她又点点头,低低的说了一声∶「谢谢!」
离开了那个女人,我的步伐摇摇晃晃,只怕自己要昏倒下去。
刚刚的那一幕不能一时里便忘掉,我扶着一颗树,在短墙上靠了下来,不能恢复那场惊骇,心中如灰如死。
我慢慢的摸到水龙头那边的水槽,浸湿了双臂,再将凉水泼到自己的脸上去。
荷西的坟就在那边,竟然举步艰难。
知道你的灵魂不在那黄土下面,可是五年后,荷西,叫我怎麽面对刚才看见的景像在你的身上重演?
我静坐了很久很久,一滴泪也流不出来。
再次给自己的脸拼命去浸冷水,这才拿了油漆罐子向坟地走过去。
阳光下,没有再对荷西说一句话,签字笔一次次填过刻着字的木槽缝里——『荷西、马利安、葛罗。安息。你的妻子记念你。』
将那几句话涂得全新,等它们乾透了,再用小刷子开始上亮光漆。
在那个炎热的午后,花丛里,一个着彩衣的女人,一遍又一遍的漆着十字架,漆着四周的木栅。没有泪,她只是在做一个妻子的事情——照顾丈夫。
不要去想五年后的情景,在我的心里,荷西,你永远是活着的,一遍又一遍的跑着回家,跑回家来看望你的妻。
我*在树下等油漆乾透,然后再要涂一次,再等它乾,再涂一次,涂出一个新的十字架来,我们再一起掮它吧!
我渴了,倦了,也困了。荷西,那麽让我*在你身边。再没有眼泪,再没有恸哭,我只是要靠着你,一如过去的年年月月。
我慢慢的睡了过去,双手挂在你的脖子上。远方有什麽人在轻轻的唱歌——
记得当时年纪小
你爱谈天
我爱笑
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
风在林梢鸟儿在叫
我们不知怎样睡着了
梦里花落知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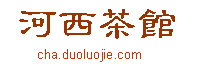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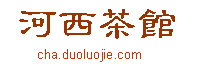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5/11/16 0:44:00
Post By:2005/11/16 0:44:00

